给朗读一点空间——南京理工大学“五月诗会”侧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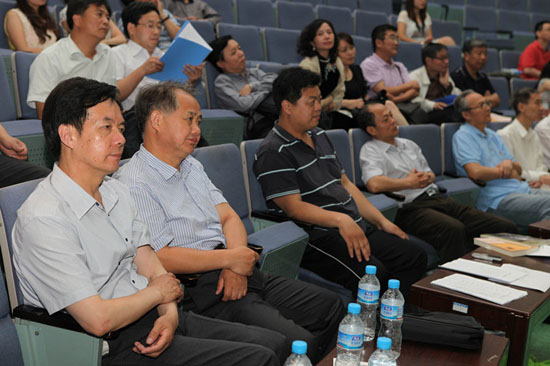
沉迷与陶醉。诗会现场一瞥

徐明德忘情朗诵《我的菜园我的歌》,屏幕上数名中年美女出没于他家菜园。
遗憾的是徐老没能扛一把锄头上场
朗读在何种意义上远离了当下生活?这看起来并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正如读德国当代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朗读者》,我们能从中轻易读出笼罩在“纳粹”、“二战”、“集中营”等沉重字眼下的反思主题,也能透过小说中纳粹女看守汉娜宁可被加罪,也不愿说出自己不会读写的怪异举动,读出让人为之动容的有关爱情、罪恶与尊严的主题,却独独忘了“朗读”本身。即使实际上唯有“朗读”才真正构成小说的核心,也不能让我们在这个字眼上稍事停留。
如此感叹,其实关乎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假如汉娜会读写,她是否还会那么热衷于听人朗读?进而言之,没有了朗读,这个让人荡气回肠的故事本身,是否还有足够的合理性,或至少在某种意义上丧失了耐人寻味的艺术魅力?答案不言自明。而这也反证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当下这个绝大多数人已学会了读写的时代里,朗读是否必要?换言之,朗读在当下是否还保有原初的意义?
或许,我们置身的现实本身,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当下,我们偶尔会在电视节目上看到诗情画意的散文诗的朗诵,也碰巧会在某些场合听到字正腔圆的普通话的朗诵。这些朗诵过滤掉了读来未必朗朗上口的诗歌,诗歌的世界由此变得单一而乏味,而作品照例会被演绎得出神入化,但唯一缺少的是真实的个性。
在这个意义上,于5月28日在江苏南京理工大学举行的“五月诗会”,确乎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冯亦同、方政、徐明德、陈永昌、海马、紫衣、陆新民、雪丰谷、海波、雷默、古筝、马永波、张宗刚等40余位老、中、青诗人先后上台朗诵自己的诗歌。这些诗歌里,有古雅简朴的旧体诗,有明白如话的散文诗,有充满诗性感悟的文化诗,有优雅、奔放而不失狂野的现代诗,有结合了晦涩意象的后现代主义诗歌。而通过主持人的解说,或是诗人们的旁白,也让你了解到诗歌后面的故事。比如,女诗人修白多年前穿婚纱出嫁那天,半路上听到有诗人在广场朗诵诗歌,即坚持停下来听,而她当年的嫁妆就是一箱诗歌。
诗会显见地体现了兼容并包的特点,诚如组织者张宗刚所言,诗会近官而决不媚官,近商而决不媚商。不拉帮结派,不搞小圈子。凡诗道同仁,无论贫富贵贱亲疏远近,均以诚相待。而更直观的体现,还在于在诗会上,你能听到没有被普通话规训的朗诵,听到夹杂了各式方言的朗诵,听到能体现个人真实性情的朗诵。而是否听明白、听懂本身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朗诵,你在倾听。这里体现了巴赫金所谓狂欢的自由精神,这里有着古希腊集会广场式的回响。
然而,这样的朗诵即使偶尔能在诗歌界看到,在国内当下其他相关活动中却近乎销声匿迹。间或,国外作家的来访使得朗读成为一个特例。去年6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访华,在上海戏剧学院的一个小剧场里为听众朗读了他最爱的《酒吧长谈》。正如当时到现场助阵的作家叶兆言所说,同样是朗诵略萨的小说,标准规范的普通话的朗诵,声情并茂抑扬顿挫,不可谓不好,但总有点格格不入。而对于略萨本人的朗诵,隔着不同的语言,我们很多人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懂不懂并不重要。听众还是更愿意听这声音,因为毕竟这才是原汁原味。
事实上,隐藏在原汁原味背后的,是作家与读者之间有关朗读与倾听的默契,是读者对于人与作品的同一性的诉求,是作者对在朗读中袒露真实性情的了然。仅此一点,我们或可期待的是,给朗读一点空间。
(傅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