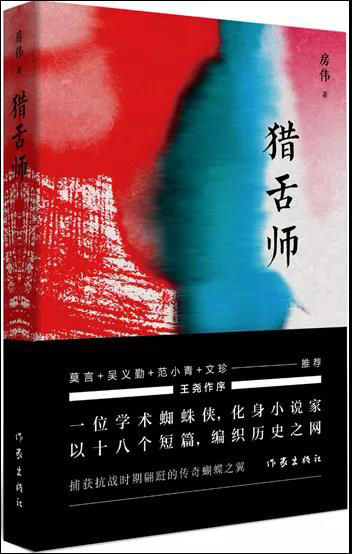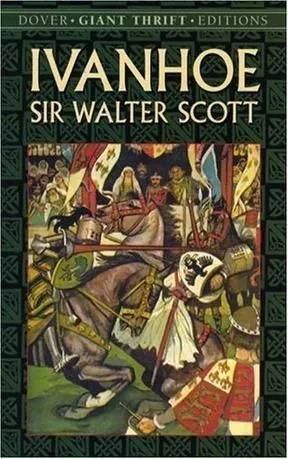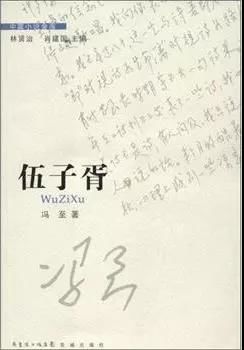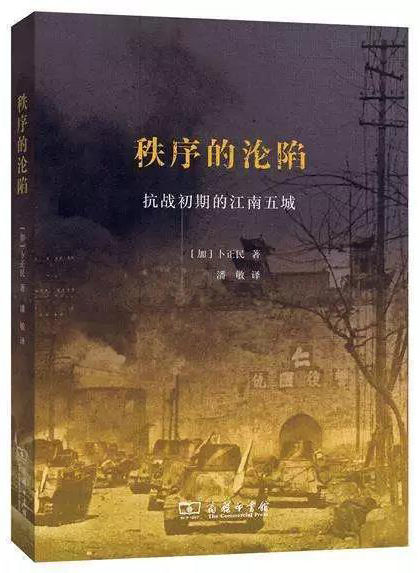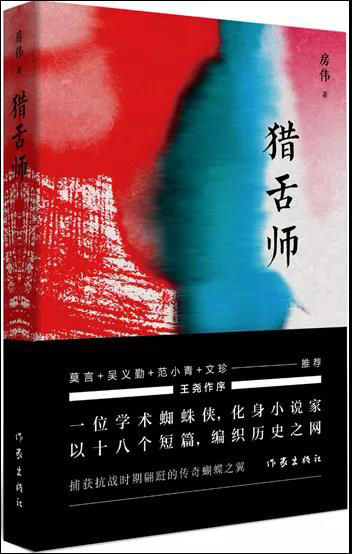
在关注房伟近几年的小说创作之前,我对作为青年批评家的房伟印象深刻。房伟对王小波和其他当代作家的研究,充满真知灼见,是他们这一代批评家中的佼佼者。房伟曾经很长时间在山东的高校任教,引进到苏州大学后,我们成为一个教研室的同事。我逐渐了解到房伟在做文学批评的同时,一直创作小说、诗歌,十多年前就出版过长篇小说。房伟这几年写抗战历史题材的小说引发广泛关注,2017年获得江苏紫金山文学奖之优秀短篇小说奖。我的感觉是,“小说家”房伟,大有压过“批评家”房伟的趋势。
房伟既批评又创作,是我理想中的现代文人的最佳状态。我曾经多次谈到,我期待自己像现代史上许多文人那样,在大学里教书,写作,写论文,写小说,或写其他。房伟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房伟的写作状态远比我想象的要好,他从容不迫,热情而不失冷静。教学、研究的任务已经很重,但还不时发表小说新作。疲惫的我每次见到毫无倦容的房伟,都要感慨他浑身散发的“正能量”。
现在即将付梓的《猎舌师》结集了房伟近几年来创作的以叙述抗战历史为主的中短篇小说。在写作这些小说之前,房伟做了大量的史料准备,又以批评家的本能选择了叙述历史的方法和形式,展开自己关于历史的想象。这样一个收集资料、进入历史情境、再艺术创造的过程,有不少值得我们关注和讨论的话题。
抗战与历史,都是当下文艺重要的关注热点,也是创作突破的难点之一。说起“历史小说”,人们往往首先想到“长篇”历史小说。通常的印象是,“长篇”的时间跨度、空间容量,及厚重历史主题,更能表现我们对“史诗性”的想象。这也是中国小说叙事传统的一个特点。《史记》之所以称为“无韵之离骚”,就是因为它不仅记录历史,而且有着文学化的构思剪裁、布局谋篇,有着文学化的人物塑造与故事编写。中国文学之中的历史,偏重其传奇性与故事性,历史观多为循环史观与帝王史观。比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这类演义小说。这种“文史不分”的情况,在西方社会也存在,早期西方史学着作充满文学笔法,比如,希罗多德的《历史》有丰富的故事细节,恺撒的《高卢战记》可看为优美的散文随笔。中世纪史学,表现为上帝意志的“历史阐释学”,有神迹等神秘主义东西。这种情况,直到兰克、吉本、蒙森、卡尔等近代启蒙史学家出现后,具有科学理性意味的“真实性”,才逐渐成为历史第一要素,文学的成分、道德评判的成分,才逐渐退出历史叙述。
这也影响到西方文学对历史的表现。西方的现代历史小说,从号称“历史小说之父”的司各特的《艾凡赫》,一直到狄更斯、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当代的尤瑟纳尔、库切的作品,都充满了理性精神和哲学意味,在追求历史真实基础上,探求人与历史与社会的复杂关系。西方历史小说,更关注历史真实性,更追求历史理性精神。也就是从一个更高的理性精神层面,来看待历史轨迹,而不是依靠某种意识形态力量。比如,尤瑟纳尔的《哈德良回忆录》,以虚构的罗马皇帝哈德良的回忆录为线索,不仅为我们展现罗马时期栩栩如生的生活场景与历史风貌,而且表现了作家对于生死、历史与存在等很多严肃问题的思考。着名西方历史学家吉本就说过,历史是由血与火、人类的罪行与愚蠢组成。这种对历史“性恶”论的观点与历史理性精神,是我们的历史文学匮乏的。我们的历史文学,除了传奇性演义特质之外,底色则有着浓厚虚无天命观与道德化价值判断立场。在此之上,则是强烈的意识形态化历史观念,历史成为意识形态图解工具。
在当代中国,历史小说多是长篇巨制,追求史诗性。这种史诗性,除了文学的野心,也有意识形态进化论的影响。新时期之后,新历史小说兴起,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对宏大叙事的质疑,但又在游戏性、戏仿颠覆的叙事方式之下,造成了历史叙述的贫弱,追求“六经注我”的自我意愿,也对历史理性造成了负面消解。很多小说把历史解读为虚无史、欲望史。这样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失去最初新鲜感之后,就因为历史理性的匮乏而陷入叙述困境。目前活跃于银幕的“抗战神剧”、“历史神剧”,除了民间的历史传奇思维,也要追责到新历史主义的负面效果。电影《白鹿原》就将一部探索中国百年历史的严肃小说化为田小娥的“骚情史”,这无疑是发人深省的。新世纪之后,史诗性的长篇历史小说再次兴起,以此表征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但似乎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很多长篇历史小说,动辄40、50万字,大多是几大家族争斗,百年巨变沧桑,或王朝争霸,成就一代明君。这些长篇历史小说,徒有史诗体量,但并无史诗的精神容量与思想含量。它们既缺乏历史反思的深刻性,也匮乏历史理性精神。所谓宏大表象之下,这些作品大多还是较保守的历史观和文学观,有的甚至还在追求所谓“雄主帝王”史观,实在陈腐不堪。
冯至 《伍子胥》

周梅森 《大捷》
好的历史小说,应是文学的感性体验与想像力,结合历史真实性与理性诉求的产物。几个方面不可或缺其一。文学史上的优秀中短篇历史小说也不少,比如,诗人冯至的《伍子胥》、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等,新时期以来抗战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就有尤凤伟的《生命通道》、周梅森的《大捷》、阿成的《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等名作,但中短篇历史小说,尤其是短篇历史小说,难度却并不小。如果一味追求灵巧,就会成为不成体系的零散片段;如果只注重史诗性,则会让作品变得沉闷不堪,丧失鲜活的个人体验与强烈的故事代入感。要在精短篇幅之中,快速进入一个感性历史情境逻辑,将读者带入到独特的历史氛围,又能在有限篇幅破除局限,展现宽广的历史视域与历史反思,这的确不容易。同时,注重历史精神,也不能放弃历史小说的娱乐性,如何将历史故事讲述得动人心魄,在传递历史真实信息的同时,给人以智慧启发与故事性愉悦,也是房伟的这组历史小说努力的方向。这些小说非常注重逼真的历史现场感的还原,细节描写的镜头画面感很强。
房伟的这组历史小说,大部分是短篇,最长的2万多字,但写法结构还是短篇的规模与气质。他的做法是当一个“蜘蛛侠”,结成“历史之网”,利用特色各异的短篇小说集合体,造成一种长篇小说效应,但又能保存每个短篇的独立艺术和思想价值,从而捕获那个飘荡的“历史蝴蝶”的精魂。每一篇都试图找到一个新的表现视角,呈现出新艺术手法,颇具匠心。有的小说颇具悬疑侦探氛围;有的灵动自如,写世情写人物;有的利用美食、惊悚等类型文学手法;有的借助《聊斋》手段,以狐鬼写人性;有的则更像历史随笔散文,淡化情节,探讨哲理;甚至有的小说,还借助符号学理论,以理论入小说,追求理论与文学文本的融合。短篇小说素有“社会生活的横截面”之说,更擅长通过细节勾勒,片段呈现与留白艺术,表现个人化叙事与日常书写,即便写历史,由于篇幅限制与题材拘囿,往往也是草蛇灰线,点线结合,“留白”大于具体“历史写实”。这样的写法,固然灵动,富于象征隐喻性,但又让人感觉不够厚重。房伟的这个系列抗战小说,可看做是历史短篇小说的“组合拳”,将短篇小说善于写“点”的特长发挥出来,以点带点,以点而细织而成“网面”,以具体历史场景“横截面”,造成对抗战历史“全景式”重新理解。虽然这些小说篇幅都不大,但从叙述空间讲,涉及日本北海道、屋久岛,越南的河内,中国的则有南京、北京、上海、苏州、扬州、济南、沂蒙山、微山湖根据地、山东莒县、香港、台湾等。
在叙述时间上,房伟小说有抗战各个时期的展现,早至1928年的济南五三惨案(作为1931年“九一八”抗战的前奏),晚至日本战败投降的故事,同时,也涉及当下现实时空对抗战的理解。从人物来讲,它包括了很多不同层面的人物,中国方面既有汪精卫、蒋介石这样的历史大人物,也有军队高层军官,如起义将领,叛逃的师参谋长,潜伏的日伪官员,日军方面则涉及副领事、师团长、大佐等高级军政人员。但这些小说更多刻画了很多非常有特点的小人物,比如,军统底层人员,投毒杀敌的中国厨师,八路军战士,根据地民兵连长,自发抗战的普通村民,内心痛苦的汉奸,自杀的日军中尉,伪军小军官,日本军医,日军逃兵等。作家试图进入这些不同历史人物的复杂心灵,不是简单“道德判断”和“意识形态规训”,也不夸大“历史的同情”,给予他们过多历史特权,而是将他们放置在具体历史情境之中,以严肃的历史理性精神,考察他们和大历史之间“晦暗难明”的关系。
这些历史小说,就是大大小小的“历史心灵”编织出来的历史,效果在于跳出国仇家恨的道德叙事局限,从历史精神高度审视这段民族国家的历史。比如,小说《手肴》再现了南京屠城的惨剧。被日军强暴的女学生和当汉奸的表哥,形成了紧张对峙关系。小说从女学生的视角,再现了表哥令人难以理解的生存意志。小说没有美化表哥的软弱妥协,圆滑世故,也没有遮蔽他残存的善良与保存同胞的善举。丑陋的战争将美丽的女学生化成斩断敌人手掌做炖菜的女杀手。人性是复杂的,面对屠杀,女学生和表哥都做出了不同人生选择。小说将道德审判和人性审判的双重权力,都交给了读者。小说对于江南地区面对日军侵袭的反映,令我们想起加拿大抗战史专家卜正民。他的着作《秩序的沦陷》就从很多史实细节为我们勾勒了众多历史小人物。无论抗日志士,汉奸,还是所谓“合作者”(cooperator),考察那段血与火的历史,既要坚持人性的宽容视野,又要予以冷峻的历史批判。
卜正民 《秩序的沦陷》
我注意到,这组小说还注重历史与现在的“互文性”关系。《指南》《鬼子妮》《还乡》《五三》《白光》等小说,都从历史与当下的联系性入手写作。《指南》以电脑游戏虚拟抗战景观,反思当下现实青年的心灵迷茫;《还乡》以女记者对抗战期间发生的悬案的访查为线索,再现了历史的多维度可能性;《鬼子妮》虚写日军逃兵在中国的生活,实写“文革”对人性的摧残;《白光》以抗战军队的鬼魂再现,写出了日常生活的沉闷无聊;《五三》以失业在家的老记者,查访爷爷对历史大事件的参与入手,写出了人生对意义寻找的重要性。小说《五三》,写到了一只飘飞于历史迷雾的蝴蝶。这组小说也出现了很多有关“雾”的描述。比如,《还乡》中的雾气缭绕的神秘大山,《杀胡》中的山瘴弥漫的小村,《肃魂》里埋藏无数尸骨的元湖上空的水雾。这雾气是历史迷雾,有无限的神秘气息,既充满魅力,又有几分狰狞,它隐藏着无数血泪,无数爱恨情仇,也隐藏着无数可能性,偶然性,人性隐秘的挣扎与晦涩哲思。“蝴蝶”就是穿越历史迷雾的心灵力量。
卢卡奇谈到小说与史诗的复杂关系时认为,史诗和小说这两种客体形式,并不是按照创作态度,而是按照它们在创作时发现的历史哲学事实区分开来的。小说的时代,生活的“外延整体”不再显而易见,感性的生活“内在性”已经变成了难题,但这个时代仍然有对于“总体”的信仰。这种“总体性”,是作家面对个人化的生存现实,面对人与自然分离的人造世界,所执着进行第一种整体建构性的“赋形”努力。伴随着中国全面的现代转型,中国历史小说必须反思其“史诗性”品质,是用一种意识形态正确的话语给予规训,还是从个人化的视角,理性地看待中国的民族国家发育过程的种种光怪陆离与酷烈创痛,并寻找出一种总体性的心灵主体状态,也许是摆在很多中国小说家面前的迫切任务。
在这个意义上,我对房伟的小说创作怀有更高的期待。(来源:中国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