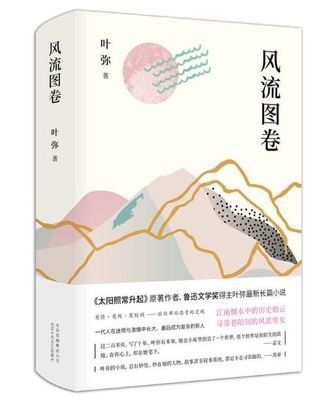
在动荡奔涌的生命长河中,漂泊的人心从此岸出发,始终渴望抵达彼岸得到安宁。在生活日常与无常的相伴中寻找自我,在吞咽世界的荒诞与惊奇的同时感知自我,然后在时间缓慢又迅猛的流逝中接受自我。每个人兜兜转转、寻寻觅觅的一生是学习成长的过程,也可谓是摆渡自己的旅程。作家叶弥一向关注现世人类的成长期,无论是青春期肉体的迷茫躁动,还是精神世界与成人话语的对垒,各色人物在她笔下灵动又倔强地破土而出,脆弱又坚强地生长起来。她的长篇小说“新作”《风流图卷》同样书写了一个以少女孔燕妮的成长为主线,勾联出几代人在时代洪流泥沙俱下的裹挟中,与残酷现实的挣扎、妥协、抗争。以及他们遭遇无法选择的命运时,如何选择自我,又如何保持自我的传奇故事。
叶弥自2008年搬去太湖边居住,2009年开始创作这部小说,计划共写四卷,写写停停,第一、二卷首发于《收获》2014年第3期。停停写写,2017年秋至2018年6月初,又重新修改,“删掉了七八万字,增补了五六万字,成为现在这个模样。修改完的那一天,我感受到了真正的解脱,无关文字,而是解脱了人生里许多妄念。……时间让我对人生和社会有了新的认识,这也是这部小说给我带来的意义,我感觉到是它引领着我成长,成长的全部内容就是识得‘命运’二字。不识这两个字,奋斗无意义。”[1]这十年时间里发生的,不仅是叶弥从城市回退到城郊后生活状态的改变,主动撤退更在于她想皈依本心,寻回自己。她在重拾文学力量的修行中,念念不忘儿时阅读《石头记》《水浒》《普希金文集》等书籍时忽然在眼前展开的绝代风流;对吴地苏州爱得深沉,也促使她想挖掘并织绣出这片水土的风流绝代。于是,历时十年,叶弥在乡土自然修炼心性的同时,也把自我追寻的成长过程,耕耘成文学作品:人物浮浮沉沉,世界花开花落,此岸至彼岸,彼岸至此岸,皆为渡,自己就是自我的摆渡人。
《风流图卷》顾名思义就是艺术地描绘一幅幅风流的英雄俊杰图。何为风流,为何风流,如何风流,都与所处的时间与地理空间紧密相关。叶弥的小说有一类完全架空背景,不提及所处时代,直接呈现社会生活某个剖面,仿佛就发生于昨天、今天或明天转角的街巷里,作者、读者与人物共情,时间与空间、现实与历史共融。而剩下的一类往往在开篇便明确指出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例如,“这是一九六七年的中国,距今不远,想忘也忘不了。”(《天鹅绒》)“八八年,也就是改革开放的第十年。”(《成长如蜕》)“李欧八〇年回到城里的时候,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土包子。”(《两世悲伤》)“七〇年春天来的,不知道为什么要来?来了快三十年了,从来不见有亲戚来看他们……”(《明月寺》)“吴郭城的大家族文家,早在1936年日侨分批撤离吴郭市,就开始出外避祸。”(《文家的帽子》)关于此类作品,有论者评价“叶弥擅长给自己的故事找一个过去的背景,让它帮衬着,或是反衬着人物与故事。……叶弥是利用了历史,但并不依赖于历史。很多作家作品钟情于描写‘大时代里的小人物’,叶弥却不直面宏大历史,再现时代风云,而是独辟蹊径,写了她自己的‘小人物’与‘私时代’。”[2]当下中国文学创作同质化很大一个根源,在于作者放弃有难度的创作,把日常生活不经过滤,一地鸡毛倾泻到作品中,放弃经典化、历史化建构的努力。叶弥迎难而上,在《风流图卷》里,她不再仅满足于“以轻击重”,而是力图以她惯有冷酷的轻盈、慈悲的爱怜,正面把特殊时代背景与人物的命运哀乐紧密连接在一起,然后试图寻索一种超越特殊时代、特殊人事之上的亘古不变的人类精神,求的是一条思想之路。
小说的上卷发生于1958年,下卷于10年之后的1968年,两个时间刻度都是中国当代史上历尽磨难的时期。故事的地理背景依然设置于叶弥的文学领地:江南富饶之地“吴郭”及周围乡间区域:香炉山、花码头镇、桃花渡、蓝湖、青云岛……熟悉的地理坐标在叶弥的各类文学作品中连接起来,共同搭建起这方水土的今生前世。
“这是吴郭市,古称吴郭。从三千年前建城到现在,气象安详。”“我”家在红旗坊里的111军医院,路口有一座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建成的石牌坊,内容令人称奇,竹梅辉映,“七夕相会”与“西厢记”相望,精致恢弘的雕刻中夹杂着粗鄙浅显的生殖图纹,成为民间风流生活的日常谈笑,“也许它的目的就是与一本正经的世界开个玩笑。”[3]古老的巷弄里,千百年来世世代代住着安分守己的人,“因为有这些牌坊和高塔在,富人便谦虚了,穷人也就不忐忑。一座塔,一座牌坊,它的顶层和基座,代表着人不能企及的高度和无法承受的重量,让人守其所安。”[4]1958年1月底,一队战士从军医院跑出来用炸弹把牌坊炸倒了。只因牌坊妨碍了进进出出的、象征着时代的权力、力量、时尚、性感的军用卡车,千百年来的文明被摧毁,建立新秩序的时代容不下无用的石牌坊。
1968年3月,吴郭城两大派系(保派、赶派)拿起刀枪为了各自的观点斗争,遍地风流化成遍地火光。文明与文化曾经随着白玉兰花的每一朵怒放,开落在这座城的每处角落,赏花、织绣、酿酒、谈笑,莲花和彩虹一般的人儿走过街头巷弄,飘荡着温软的喃喃细语,风花雪月、香甜丰满的市井,现在已经不复存在。街道上狼藉的是明清时代的废砖碎瓦,游走的是不长眼的流弹。城市看起来会一蹶不振,难现风采,然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时间与地理在人的调和下以强大的生命力修复伤痕。“虽说不久前吴郭刚经历过一场混乱,但爱吃爱玩的吴郭人很快就恢复了热闹”。[5]每个时期的动荡终会过去,真正风流的不是时间与地理,而是身处其间追求真善美的生生不息的人。
小说在1958年庆祝吴郭解放9周年的礼炮声中拉开帷幕,15岁的少女孔燕妮从梦中被吵醒,以第一人称展开了一幅漫长的时光图卷。纷繁的故事围绕着她以及她的家人、朋友展开,勾勒出一个少女以及几代人在特殊时代裂痕里的自我探索、挣扎着奋力伸展的风流。时代浪潮的危机四伏,从父亲孔朝山写给柳爷爷的信中已经显现:
我没理他,继续朝下念:“陈从周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还在同济大学里接受大家批判。汪曾祺、丁聪、聂绀弩也成了右派。汪曾祺在河北张家口农科所画土豆。丁聪和聂绀弩到了冰天雪地的北大荒接受劳动改造。储安平被送到长城脚下去放羊,听说日子倒也还好,天天用铁罐子装羊奶喝。还有吴祖光,成了反革命右派分子,今年他也要被押送到北大荒了。你还记得许宪民的女儿彭令昭吗?许宪民带着这女孩子来看过你的。你记得吧?这女孩子后来考上北大中文系,改名叫林昭,她也成了右派了……”
柳爷爷抬起头说:“你不要朝下念了,我对这些不感兴趣。我的这些老朋友小朋友,对政治的兴趣远远大过对生活的兴趣。[6]
这些闪闪发光的名字都是吴郭文化名流柳爷爷的旧友,而他们此时的遭遇预示着当时的政治环境,以及柳爷爷即将可能面临的险状,可他却显得毫不在意。这位奉行享乐主义的“老古董”刚搬进中西合璧的园林建筑“廿八斋”不久,雕廊画柱,开门见水,尽显风流。这种风流不仅彰显在红楼梦式的绿梅雪泡茶、玫瑰油洗头、羊脂白玉压书等极致讲究的生活方式,还在于他对快乐的精神追寻,“中国人太看重悲哀的力量,不看重快乐的力量。快乐地活,才是最有力量的事,才是一件有益自己、有益别人的事。”享乐是身体和灵魂的双重需求,“一个不知道自己需要的人,不会知道别人的需要。一个不懂得关心自己的人,也不会真正关心别人。”[7]
柳爷爷享受了大半辈子的快活,潇洒风流抵不过政治的风向,它要否定一个人的生活,“要打倒他和他代表的生活方式”。柳爷爷被人假传指令戏弄,经过一番农场和监狱的乌龙回到家中,身心疲惫,虽然定彩朴实的真心与肉体给予不少安慰,但文化人最在意的脸面与风骨已经遭受了难以容忍的羞辱。院子里假山下,堆得高高的柴火,柳爷爷抱着将开的昙花,隐没在火光之中,留下一句“我这一辈子最讨厌的就是‘改造’二字。”昙花一现,生命坍塌。“廿八斋”的门口,被人涂上八个红漆大字:生的有趣,死的夸张。
这八个大字不仅是柳家骥一生的写照,也是叶弥笔下这些风流人士的命运缩影。一代风流,前仆后继,奔向死亡,奔向自由。柳爷爷高调又夸张的行事是其坚守个人生命意义的方式,既然旧时代的石碑已被革命摧毁,那么他甘愿成为旧文化的殉道者。如果说柳爷爷扞卫的是文化和思想的自由,那么常宝的死,则代表美的自由被抹杀。
常宝——“医院里的药剂师,三十几岁,至今未婚,一个臭名昭着的风流女人”。作者在文中直接描写常宝的篇幅并不长,但是她似乎又无处不在。“常宝的事,我稍后再说”,四次悬念,让人物未出场已经引人期待。常宝柔声细语,热爱生活,摇曳生姿,在军医院家属大院的口舌唇齿间被异化成一个女性风流的另类。常宝毫不掩饰自己的软弱让“我”怒其不争,可是她莫须有的死亡,却让“我”哀其不幸,更加速了“我”成长的叛逆与对人世人生的怀疑。她是一个妖娆又脆弱的导火索,让时代的荒谬、人性的复杂、美的吸引力逐一爆破,并且串联起时空的种种面向。这个美好的皮囊在批斗会上任人践踏,所有凝聚着女性追寻美丽的器物在此时都成为“犯人”的呈堂证供,发光的旗袍、细腻的丝绸衣物,特别是那些开司米钩织的胸罩,以一种正大光明接受批判的方式散落在台下看客的眼睛里,并飞快地在心底深深扎根。4天之后,美的自由,在“我”眼前被枪毙了。讽刺的是,之前的被冠以种种罪名的常宝,在死后却成为一种摩登的生活方式,作为对美丽极致追求的象征成为吴郭女性生活中经久不衰的模仿样本。
常宝的幽魂在白玉兰的层层叠叠中跟“我”说:“你将来会知道,你做的所有事,统统没有用。”柳爷爷的女儿如一师傅也回答“我”:人做的一切事,可能都是没用的。“我”甩开如一姑姑的手,就像甩开常宝的手一样,她们的软弱让“我”失望。如一和明心二位师傅,两小无猜。再见时,如一在香炉山的止水庵,明心在旁边的梅积山重建了修远寺。近三十年的时光里,两人共修佛法,两山连通廊桥,佛法温柔,佛心多情。也是在1968年,两派的械斗动乱蔓延至香炉山,修理宗教信仰的自由,两人共生共死,下山寻觅救兵之后再也没有回来。只留下街头巷尾说唱人口中的风流唱词,口口相传,永存于世。也许如“我”所想,“听了这戏中的唱词,我就明白如一和明心,不可能还活在世上”;又或许他们就在1970年逃到了叶弥笔下的《明月寺》,还俗成为“薄师傅”与“罗师傅”,守着二郎山的日出日落隐世30年。世上都是软弱之人,“我”不爱看到人的软弱,她们应该坚强地找到一切方法活下去。
与常宝和如一的“脆弱”相比,高大进奶奶在吴郭口口相传的传奇里,是一位时尚的革命者,她以极端“刚烈”的方式守护爱情的自由。无论是在延安时擦枪走火打死了挚友和情敌双重身份的小张娃娃,还是回到花码头镇之后与“老丝瓜”司立新缱绻多情的姐弟恋,高大进并不在意他人的眼光,随心所欲,对人有情。她为了民族的自由与解放,回到娘家后,脊梁骨挺得直直的,泼辣又果敢,分土地,分房宅,每日在居委会做工作,深受村里人的爱戴。1968年,奶奶被曾经工作过的居委会押回老家批斗,批斗会结束后,奶奶与“老丝瓜”一同吃砒霜殉情自绝。“我”把两人葬在一起,以期让他们的情爱达到某种永恒。十年前,奶奶被接回吴郭前,两人偷偷在芦苇丛里搂得紧紧的,陶醉得红了脸。“天空有两只大蝴蝶风筝随风嬉耍。生物柔软,死物僵硬,它们如此柔软,把生的特性模仿得惟妙惟肖。”[⑧]此时,风筝远走高飞,相爱的人却永埋地底了。
“人要知道快乐,才算是一个人。”在青云岛上济世救人的陶云珠大娘同样奉行性情自由的生活方式,因传授青年男女相爱阴阳之道,被“破四旧”扔到湖心除掉了。云珠14岁时被吴郭前清举人余自问收在身边当使唤丫头,跟着余家见过多少风花雪月,上海的文学沙龙、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曾朴的《真善美》……文化风流的种子在她心中生根发芽,夜不能寐,就像余老爷说的“因懂得真善美三个字,活得也算像个人了。”陶大娘用了一周时间把这些风流人物的故事讲述给干儿子张风毅。
深爱孔燕妮的张风毅跟随着姐姐张柔和在“廿八斋”生活时已经深受柳爷爷享乐主义的影响,此时,这些绝代风华更激荡着这个年轻的诗人的心,他写下《曼娜回忆录》,“不管这个曼娜是谁,她一定是追求自己幸福的人。这位叫‘曼娜’的女性是男人们一生倾情的女性。他要告诉世人,这位了不起的女子怎样为了个人幸福而奋斗,怎样在严苛的环境下伸张自由的精神。当然,她还必须承担教化男女的任务,就像干娘一样……张风毅写过好多诗,从没有写过小说。以他的理解,在这样的年代,小说应该是直抒胸臆的,越是坦白,对人的生活和灵魂就越发有用。思想在此时并没有那么重要。”[⑨]在“我”的建议下,《曼娜回忆录》装进漂流瓶,最后,竟从蓝湖出发飘荡成人人相传的集体创作手抄本,在封锁的时代满足了许多人对风流的想象。
所有的宗教都是我的宗教,
所有的爱情都是我的爱情。
快乐是世上最崇高的理由,
宽厚是生活最合理的动机。[10]
这是创作《曼娜》十年前,少年张风毅写下的诗歌,当时的“我”想:“从他的诗里看,他深受柳爷爷的影响。话说回来,我们谁不受柳爷爷的影响呢?”孔燕妮在故事的开始便承认柳爷爷对她的影响,同时,天性里美男子父亲孔朝山对爱与美的崇敬、对人的宽容;与革命典型母亲谢小达所代表的大时代中“成为一个战士”感召所需要的炽烈、勇敢、坚强,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在其生命血脉中激烈撞击。这个诞生下来便被炸雷之后的彩虹加持的“仙女”的成长历程被赋予夸张的传奇色彩。
孔燕妮的自我成长正是“渡己渡人”,摆渡自己,超度别人的过程。小说中具体表现在她在各种程度参与了上述风流人物的人生历程,各种风流在这个少女的精神世界中混沌地纠缠在一起。作者从母女关系、身体的成熟与精神的自我救赎等几个方面来表现政治环境中青春期女性的成长。周围政治环境对身体的侵略与迫害,常宝死之后她决绝地把头发剃光以示对不公正死亡的反抗,友人唐娜在厕所的大镜子前教会她对自己身体的认识。1958年,政治的浪潮中,她在月经初潮中,开始了真正的人生之旅。温暖湿润的生命萌发,在月色如水的浩渺宇宙中,唤醒她对生命神秘与命运意义的探索。人活着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贯穿了全书。生活在这个国度里的孩子们,往往还没做好成长的准备,就被抛掷到成人的世界里,被迫接受了种种成人法则。孔燕妮是坚强又软弱,她经历了种种苦难,重重风流,从依赖外界力量地救赎,例如极度渴望获得母亲的认可和男性身体的慰藉,再到后来可以自己做主自己的身体,自己寻找到精神的出路。她终于在一次次声嘶力竭地身体探索与生命叩问中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与重生,终于她完成了自渡。这是一个漫长而反复,甜蜜又痛苦的摆渡旅程。
“小说艺术,其实就在虚与实、隐与显之间。叶弥擅长探索人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和独特性,而所谓文学的‘减法’,就是辩证地对待这一探索,不仅是‘以无厚入有间’的纵横捭阖,更在于自觉到手中的那管笔‘止于所当止’的谦卑。”[11]在《风流图卷》中,叶弥写作的姿态不同于以往《桃花渡》《香炉山》等中短篇代表作中的飘渺灵动的随性,她在这26万字的篇幅中布下了局,正如在《后记》中写到的,不能只靠灵感写作,要靠全盘的构思,构思小说的思想,也就是灵魂。稍显可惜的是,在中短篇创作中极擅长留白的叶弥到了长篇小说的布局中,虚与隐的余味却略被填满了。在展现人物精神成长的混沌迷茫,和发现生命意义的遍地欣喜时,本该以人物行为顺其自然的展现和留有“空白”的叙述达成。而行文中孔燕妮对自己寻找重生意义和出路的自问自答,显现出过于饱满和明显的觉醒焦虑,思想的重量有时会越过故事的发展,落入纸面呐喊。
除此之外,叶弥依然保持了其生而为文学的强大艺术表现力,脚踏实地又灵动摇曳的语言让复杂的人生不拘一格,相互联通。这些义无反顾追求人间真善美,追求爱,追求个人幸福的人们才是时代生活中值得书写的风流,他们在怜花巷的作坊里,在墙缝的情书上,在古董烟枪的吞云吐雾里。有趣的灵魂被叶弥找到,并在人物的生命中生根发芽,各色人物的叙述主线在庞大混杂的时空描绘中忽隐忽现、相交相错,却能清晰地贯穿始终,而全景式的宏阔格局容纳了大量社会生活细节的生生不息与鸢飞鱼跃,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一幅既独特又光彩绚烂的风流图卷。政治挤压的缝隙间,这些在“我”梦中被老和尚如预言般下了判词的“无根的花”,漂泊无定,却极力地生长,挣扎,在遍地“彼岸花”的竞相开放中,以各自的生命方式坚守自己文化、生活、信仰、爱情、性情的自由,求得精神上的“引渡”。沉郁的时代之歌,带着一致化的蛮荒,而身处其中鲜活的人们并不是所谓的“英雄”,他们只想追寻本心,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命理解,当二者矛盾时,这些各有缺点的凡人只能又哭又笑、无可奈何地抵御侵蚀。无论什么时代中,人类对快乐对美好对爱的追求永不会变,“只要符合人对真善美的追求,任其怎么复杂,大家也趋之若鹜”,他们靠着这样的信念,在时代的长河中用永恒风流的人性追寻,摆渡自己与现实的关系,求得一个平衡,一个归宿:“中国人几千年来就是这么慌乱地跑着,跑来跑去地寻找前途。柳爷爷那时就说,人的弱,全在于没有正确的思维方式。那么多人上下求索,求的就是一条思想之路。” [12]
在小说结尾钱塘江周而复始的潮水中,这些“无根之花”平静下来,孔燕妮认真地大喊“我是自由的!你是自由的!”,如同《叶甫盖尼·奥涅金》里塔季扬娜那一声呼唤:“我恋爱了”。这份焦急地渴望着真正的成长,对自己本心的理解,历经磨难获得身心解放后的欢愉,如第一片初雪,第一缕春风,雾气散开后的第一抹晨光,第一次忽然感知到心脏的跳动与融化般,令人感动。而一个平静的独立的自我终于在主人公一次次呼唤重生之后,在读者的期待中,在叶弥瓷实而飞扬的细节描写中,随着“潮水拍击,狂风旋起,卷千重雪,挟满天雨”,如期而至。
注释
[1]叶弥:《风流图卷·后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439-440页。
[2]朱红梅:《在哪里独自升起——关于叶弥》,《南方文坛》2017年第4期。
[3][4][5][6][7][8][9][10]叶弥:《风流图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58页,第241页,第351页,第17-18页,第21、31页,第192页,第343-344页,第44页。
[11]金理:《这些年,读叶弥》,《南方文坛》2013年第4期。
[12]叶弥:《风流图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