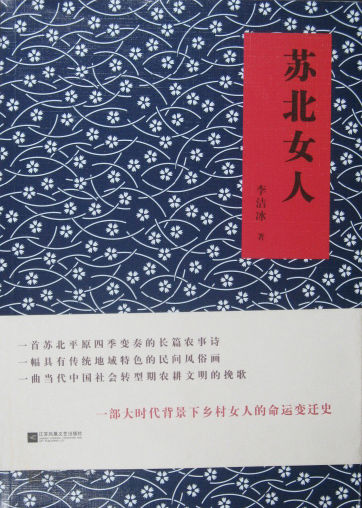当代小说对于女性群像的地域性书写,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它要求作家至少拥有四个维度以上的后援,一是对于女性的情感世界和精神方向有深切体悟,二是对于人群与地域的依存关系有深入解读,三是对当地历史积淀与族群脉动有透彻理解,四是对于叙事立场与书写方式有独到追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由江苏凤凰出版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女作家李洁冰长篇小说《苏北女人》,向小说坛提供了新颖而有意义的文本。作品以女性绵密柔韧的叙事语体,展示了中国北方乡村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至本世纪初始十年的沧桑图景;以苏北僻壤端木村为画卷轴心,塑造了柳采莲等一批极富地域性格的女性形象。她们犹如特殊物种,在现代化碾压农耕文明的进程中,顽强地支撑起男性迹近缺席的乡村生存场域,演绎出一部苏北大平原现实版的乡村农事诗。在世纪之交的历史转型期,这些女性深陷农耕、家族、社会与生存矛盾谷底,从茫然到承受,从毁灭到挣脱,命运起伏,恩怨纠结,生死歌哭,荡气回肠,展现了东方女性异乎寻常的生命坚韧度,丰富了当代文学人物长廊。
一,李洁冰对苏北女人在当代乡村生存场域的性别质地与角色定位,从作家的女性立场作了深入探索;换句话说,即“补天意识”在作品女性形象系统中的悲情体现。
补天,源于东方神话中的女娲。洪荒时期,“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刘安在《淮南子·览冥训》中描述的“女娲补天”,将上古传说中的女神及其壮举深深烙印在传承千年的汉文化中,以至对于众多女性而言,差不多演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即当灾难降临,不寻男性来一柱擎天,也不茫然四顾,而是挺身而出,勉力担当,哪怕身涉险境,也不惜铤而走险。这种文化的旨归,构成的是“女神→女英雄→女豪杰→女强人→女汉子”逻辑链。但是,就现实生活而言,女神早已隐形;女英雄、女豪杰生成的土壤也很有限;而女强人、女汉子虽不鲜见,却不外是社会心理标签化的产物。如果李洁冰按照这个逻辑链创造笔下人物,便可能落入习见窠臼。因为从女神到女汉子,无一不是文学形象的类型化。在长篇小说《苏北女人》中,李洁冰破解了这个貌似有理的逻辑链。在作家看来,第一,无论女神还是女汉子,无一不是女人;第二,女神很可能渴望走下神坛成为女人,而女人,无论被动与主动,又焉知或何曾不想成为女神?作为一种意识,它必定像秋千一样来回震荡。这样,李洁冰便找到了笔下人物在文学层面立足的基石,使柳采莲、孙二娘、闵玉镯、柳采菊以及春分、立秋等苏北女性,首先作为女人生存、生长和生活着;其次,在“天不兼覆”的社会转型期,命运将她们推上特殊的社会定位,以女性角色“炼石补天”。
那么,李洁冰书写的苏北女人,是怎样扮演生存天空“补天”角色的?长篇小说《苏北女人》书写了中国北方乡村长半个多世纪的社会运行轨迹,揭示了身处变迁中的苏北女人如何为生存而“补天”的内在动因。作家笔下的苏北僻壤端木村,“祖辈尚秦风”,历史因袭深厚;自然资源则反之。这种自然与文化生态的互动,使满口“上古雅语”的女人们的命运呈现出特殊的肌理。当然,如果用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的理念来观照端木村,会发现它基本能够对应梁氏描述,即村中亘古存在的伦理本位与职业分立[i]。在村里,亲族血缘关系差不多涵化了所有人际关系,“采莲远房的二叔公”端木善清相当于族长;职业的分立则受搏取生活资源膂力的制约,
端木福生等男人主要与田地打交道,柳采莲等女人则负责衣食起居与生养哺育。这种模式长期覆盖着中国乡村的农业自然经济形态,在柳采莲嫁到端木村福生家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依然如故。但是,随着以工业及后工业文明为表征的现代化对农耕文明的挤压与冲撞,时间序列里苏北大平原的社会分工开始变异。连端木福生家的小冬至后来也看出家庭分工发生了微妙变化:“爹闯外,娘管生娃”。“娘管生娃”自古而然,但“爹闯外”却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至今中国大部分乡村的现实缩影。变化的诱因,源自生存压力;具体到作家笔下的苏北女人柳采莲,则是盖屋与生男孩而不得的恶性循环所欠下的巨额债务。
意味深长的是,如果将《苏北女人》开篇让柳采莲的丈夫南下广东视为小说叙事所需要的“蓄势”,则很可能与这部长篇小说的题旨擦肩而过。事实上作品这样的起笔不仅拜残酷的现实所赐,还缘于李洁冰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乎男女构成体系的认知。《易传》谓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即阴阳二爻。自此女引为阴,为坤;男引为阳,为乾。乾坤所指天地,能指男女。那么就苏北平原上的端木村而言,福生等男人外出务工,无疑意味着众多家庭出现了“天不兼覆”现象。由于乡村自然经济中的生存要素,并不因为男性的缺席而递减,所以柳采莲送走丈夫后无法规避的使命便是,以女性之躯扮演男性角色,担负起在田野里春耕、夏收、秋播与冬藏重任;同时,还必须履行女性义务,不仅“管生娃”,还要哺育、教养子女和维系家庭。从这个角度看,作家笔下的苏北女人面临的“补天”的社会定位,似非意识主动的产物,而是演进中的历史机制带来的被动承受的结果。这从《苏北女人》为柳采莲等女性安排的重要事件折射的生命历程,可以清晰地透析出来。
第一,女主人公柳采莲的“炼石补天”,有一个从被动到主动、从茫然到毅然的过程。端木福生南下广东后,孕妇柳采莲为不误春耕,只能央村妇闵玉镯、孙二娘相帮。三个女人牵着老牛走向苏醒土地的情景,遂成为苏北农耕的时代象征。这些互助中的女人甚至没想到耕地需要备好犁铲,其懵懂、酸辛与无奈可见一斑。但秋收时节,柳采莲已经成为田间熟手,机械人一般扛下所有的农活。在承包“水淹地”问题上,她已经不需要征求外地务工丈夫的意见,便自主决定了男人也会踌蹰的大事。妹婿闫宝山的妻子因戏而死,善后事宜束手无策;又是柳采莲出面为胞妹讨公道,并最终大度决策。面对村里讨要“水淹地”费用的蛮横抢粮者,这个苏北女人以死相拼的勇气足以令人生畏。特别是她带着几个村妇到东北讨要丈夫工薪的劳师远征,更是非凡胆魄的彰显……这些现象所昭示的苏北女人的“补天意识”,透析出的却是令人沉重的乡村格局,即男人的缺席。因此,柳采莲的不退缩实际上是退无可退:只能是她春耕秋收,只能是她撑起家庭,只能是她为投河的胞妹出头;但是,当务工男人被骗得空手而归时,陷入幻灭的柳采莲开始知其不可为而为,表现出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执拗,凭借着本能的勇气踏上了令人揪心的讨薪征程。
第二,无论茫然的被动还是毅然的主动,柳采莲“炼石补天”的结局,都注定是悲剧性的。农事让女人走开的千年传统,被李洁冰终结在了世纪之交的苏北大平原上。春耕本非女人优势,秋收亦非女人擅长,因此柳采莲力有不逮、闵玉镯被牛踩伤,几乎是必然的。村里设计的“水淹地”契约,因有赖于“望天收”而具备了赌博与讹诈属性;柳采莲和丈夫除了卖粮还账,并无解套良策。特别是她带的四人讨薪团在男人世界的工地上沦为义务伙夫后,境遇更为不堪:两个为谋生存堕落风尘,两个一无所获铩羽而归。这不是作家的冷酷,而是她的悲悯。这种近乎残酷的情节构置,源于李洁冰对人性在道义崩坏的现实中变异的深刻体悟。惟其如此,在看到身心备受伤害的讨债人柳采莲两手空空,终于踏上故土端木村,因为百感交集而大放悲声,唱着拉魂腔回到家里时,读者才会唏嘘不已,甚至情不自禁,与面前的苏北女人一起泪奔。柳采莲的长歌当哭,是长篇小说《苏北女人》的叙事高潮之一,也是人物塑造最具创意的华彩乐章。情之所至,呼之即出;它对于世纪之交的中国痼疾戕害善良人性的揭示,抵达了小说艺术的至境,同时也是李洁冰成为一位优秀女作家的文本标志。
二,李洁冰发现并构建了苏北女人的地域性格,探索了这种性格与乡村女性命运之间的多维联系,并为苏北女人在当代小说人物长廊中出色完成了地域塑型。
以地域性别来命名长篇小说,需要作家在艺术创造上有相应的自信。由于此前李洁冰已经有《乡村戏子》、《青花灿烂》等一系列书写北方乡村女性的长、中、短篇小说创作的积累,加上人生历练的积淀和作为女性作家的优势,让她有勇气从容挑战《苏北女人》这样的长篇作品。其挑战性表现在对于苏北女性地域性格的发现与塑型两个范畴。那么,苏北女人究竟是怎样的女人?在李洁冰这部作品问世之前,鲜有作家从长篇小说角度作过系统观照。但当柳采莲、柳采菊、闵玉镯、孙二娘、春分、立秋与小满等人物鲜活、可信地来到面前时,你不得不承认,作家在为苏北女人作地域塑型的努力中交出了令人信服的答卷。
女主角柳采莲,是坚忍一脉,类似时下流行语中的“我若不坚强,脆弱给谁看”。因为丈夫或者不在身边,或者虽在身边亦形同废人;对于柳采莲来说,不待的是要“抢”的农时,待哺的是四五个年龄参差的孩子。从新嫁娘做到曾祖母的坎坷过程中,我们不会忘记柳采莲怎样让端木福生为她端了七夜尿壶,却“挪不近新娘身畔半指”;不会忘记她为生男孩如何在床第间配合丈夫,“实在捱抑不住,便央告对方停下,上面正忙着传宗接代,哪里肯住?被女人劈面一耳光,软了。”当然更多的时候,这位苏北女人有定力,有方向感,性格执着,心里装得下大事,敢于决策和行动,并且能够隐忍。所以尽管端木福生日渐羸弱,家庭却不仅没垮,还谱写了令人感喟不已的生存延绵乐章。
女人男相的“母夜叉孙二娘”,是侠义一脉。这位苏北乡村女子,性烈如火,敢于担当,使得动耕牛,“抵得上三五个壮汉”。据说祖上出过御林侍卫,所以她能凿后生五仁的脑门、敢抽端木福生的耳光,可以把窝囊的闫宝山骂得狗血喷头,将几欲偷腥的孙领班揪住脖梗朝前一送……每临大事,孙二娘的当头棒喝,总能让畏首畏尾的男人雄起、汗颜或无地自容。
乡村花旦柳采菊,属烈女一脉。她是七里屯戏班子里的头牌,过人才艺傲视同侪,亦因唱戏绝命天涯。河渚煤窑演艺队成了她命运的不幸拐点。当煤老板龚七运父子将“老少通吃”的污名罩定她,而实际境遇却是老少都不待见时,这个早已失去戏台,形同活尸的苏北女人,只能以投河的方式告别世界,以此换回生命尊严。
灌河女子闵玉镯,是风尘一脉。作为端木全村妇女的“公敌”,她曾经为胡发垠生养两个儿子,并养尊处优;但实际上,她只享有胡老板原配的名誉,早被丈夫的外遇莫桂朵架空,成为一座洋楼里的弃妇。她跟采莲形同姊妹,以与后者老公有染的方式,生下了过继给端木福生的儿子银锁。骨肉相送,道义上却没有立锥之地。洗头妹看似轻佻的表象背后,掩抑着一桩风尘女子的舍身义举,同时折射出了苏北僻壤畏香火断代为天遣的残酷真相。洗头妹出身的苏北女子闵玉镯来去漂泊,行踪不定,但每次登场,总能触动读者牵挂的心。特别是潦倒的老板丈夫洗劫式的最后一骗,让这位命运悲苦的女子最终成为小说中光彩夺人的艺术形象。
作为李洁冰笔下的第二代苏北女子,春分、立秋、冬至、小满乃至兰花等人,也个个形象饱满。春分作为“端木家的大闺女,直拗,寡言,万千的主意都闷在心里”。被迫辍学时,她会绝食抗争;丈夫染赌败家,她以“毒酒”助其戒赌;冯二前妻留下的孩子身染重病,她倾情相救;弟弟出国打工所需的巨额押金,她更是倾力援手,令人不由肃然起敬。立秋更不消说,作为戏痴柳采菊的嫡亲传人,才情丝毫不输乃师,其人生行状犹如蒲松龄笔下的怨女,波诡云谲;她像四姨一样跨越人伦常态,径直走入与世俗对立的精神空间。这个苏北女人命运的起伏跌宕,足以令风云变色,让读者叹惋。冬至、小满与兰花,作家着墨虽然不多,但她们所走的三条不同的人生道路——冬至嫁作台商妇、小满以知识改变命运、兰花将孤老婆婆逼出家门——不仅富有时代特点,而且无一不受血缘与地缘因素影响。
需要辨析的是,李洁冰笔下苏北女人的地域性格表现出的诸多形态中,起主导作用的性格是什么。细察作品中的女性群象,我们不难发现,无论她们的个性如何复杂多面,人生历程如何像作品中的村名一样呈现“八条路”,却有一种核心的性情在起作用,那就是“杠”
[ii]。“杠”是苏北方言,意谓女人说话戗,性子烈,做事认死理、不服输,不够温柔婉转,不会小鸟依人,与江南女子的吴侬软语、细腻甜糯正好形成反差与对比。《苏北女人》昭示我们:“杠”,是统摄地域性格诸面的灵魂;倘觉意犹未尽,以“杠”为圆心向外延展,则苏北女人的地域性格里必定会有“大度”二字。“大度”的字面不难理解,与港台语汇里所谓“神经大条”近似,不仅粗犷,而且拿得起、放得下。能够如此,又注定与“隐忍”相关。因此,“杠→大度→隐忍”,在苏北女人的地域性格中是相互渗透、相辅相成和互为表里的。外化为做事方式时,即前文所谓“补天”;当地方言谓之“扛”,亦即顶得住压力、认得清方向、临危不惧、遇事担当。从性别取向上来说,由“杠”而“扛”,虽然适配人类学中的男性化语境,却是苏北女人典型的群体性格表征。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苏北女人为什么就那么“杠”?怎么就那么能“扛”?作家李洁冰在小说中至少为读者作了两个角度以上的揭示。第一,是历史地缘使然。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冯友兰1947年在美国宾夕凡尼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时,曾就大陆国家的地理与经济背景对职业分立与社会心理的影响作过阐释,其理念或可为我们理解李洁冰笔下的女性形象提供参照
[iii]。《苏北女人》中有很多笔墨写到端木村的地缘特征。首先,是平原广袤。虽然端木村边有“子贡湖”,但湖的典型特征是静泊,因此与江河密布的南方水域不同,端木村民只是傍水而居,因而安土重迁;二是由于族群并不随水而动,自然以农为本、重农轻商。其次,是历史久远。察及“子贡湖”边“端木书台”由来,可知子贡曾“约孔老夫子在那里参禅论道”,因而村民深受鲁俗濡染。平原少水,则民性沉重,少动尚仁,敬理崇礼,便埋下了地域性格中“杠”的基因;源于鲁地的儒学经世致用、入世进取的理念,使苏北女人“杠”的性格外化为“扛”,是一脉相承的。第二,苏北女人由“杠”而“扛”,还缘于她们对于男性的不满。生成这种不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男性难以顶天立地,不是迹近缺席,便是羸弱不堪,像糊不上墙的泥巴,无法不令女人失望。比如“爹闯外”,非但没解决经济问题,反而搞垮了男人身体,使女人对“闯外”希望的寄托,变成了彻头彻尾的黑色幽默。二是少变通、不灵活的地缘性格,不唯影响女性,男性亦不能幸免。憨直性格使他们在市场经济环境里频繁上当。如莫桂朵的花言巧语,配上诸如搬山填海,“北海战略开发”之类的冠冕谎言,便轻松搞定了端木福生等木讷男人。
对于人类而言,生存与繁衍永远是一部厚重的大书。作家笔下的柳采莲等苏北女人,是在艰难翻动书页的过程中完成了性格的地域塑型,并有力展示出地缘性格对于自身命运走向的钳制与影响。柳采菊的投河自尽,貌似为情所困,实则性格使然。与她沉醉其中的诸多大戏相比,龚七运与五仁赐予她的挫跌不过小巫见大巫。但是,这个苏北女人的性情品位与精神高度,使她无法接受世俗的玷污,宁可以死诀别尘世。性格内向的春分被冯二折磨得得走投无路时,曾经回娘家讨教方法。也许千百年来的女性世界里确曾存在某些驭夫秘笈,比如云贵川隐秘流传的“女书”所承载的信息,比如苏北鲁南让新郎为新娘端七夜尿盆之类。但是母亲柳采莲却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告诉苦命的女儿,她只好洒泪折回,凭着隐忍与大度,以善报恶,以德报怨,感化丈夫。闵玉镯能够在胡发垠、端木福生、柳采莲和莫桂朵所构成的人性乖戾的矩阵中命运多舛而不失情义,同样缘于她的隐忍与自我救赎。冬至的命运是否像弃妇闵玉镯一样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位聋哑女子仅凭聪慧似乎难以破解台商所构建的候鸟式婚姻困局。唯有考上博士的小满,为苏北女人的命运走向带来一抹有限的亮色。而她风烛残年的母亲柳采莲,在大开发的浪潮摧毁了她惟一栖身的家园后,却依然要顶着纷扬的大雪,奔走在年关将近的乡村与城市之间,为儿子筹措出国的劳务费。这个苏北女人,几乎一生都在借钱;借钱的道路弥漫在风雪深处,仿佛永无尽头。苦难深重的女性,对于生命的意义,对于世界的意义,无论怎样书写都不会过分。但是李洁冰并不想像马尔克斯或许地山那样,让笔下的女人在道德制高点上捷足。在长篇小说《苏北女人》成书之前,据悉作家曾经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徒步跋涉在苏北平原与丘陵地带,对苏北大地上匍匐劳作的女性的生存况味,有深切体察。因此我们相信,作家笔下构建的令人不安的生存图景,是严格遵循了生活的铁侓的。
最后要说的是,李洁冰在长篇小说《苏北女人》中,还以劳动为介质,对人与土地、人与季节、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作了深入探讨,构建了女性与自然的同质性,体现了作家与先祖传统文化契合的天人合一宇宙观。同时,作家还积极探索女性书写的立场与方法,并形成了小说叙述语体独特的个人风格,从而使《苏北女人》成为作家近年来的代表性作品,也是文坛的可喜收获。当然,这应该是另一篇文章讨论的内容了。
(李惊涛:学者,作家,评论家。着有文学评论集《作为文学表象的爱与生》《文艺看法》、长篇小说《兄弟故事》、中短篇小说集《城市的背影》《三个深夜喝酒的人》、散文集《西窗》;音乐舞蹈史诗《千秋计量》等行世,现供职于中国计量大学人文与外语学院)
[i]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第2版,第61、65页。 [ii]刘传贤,《赣榆方言志》,赣榆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9年1月版,第98页。 [iii]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2月1版,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