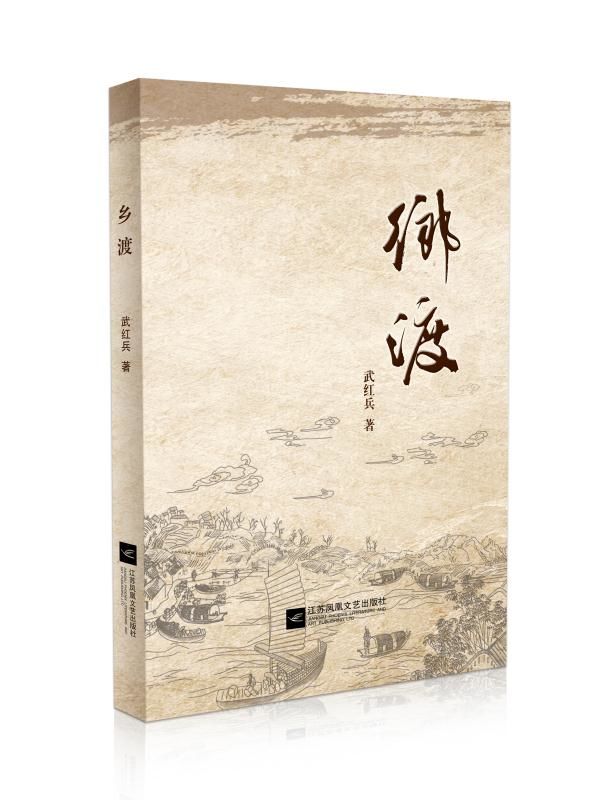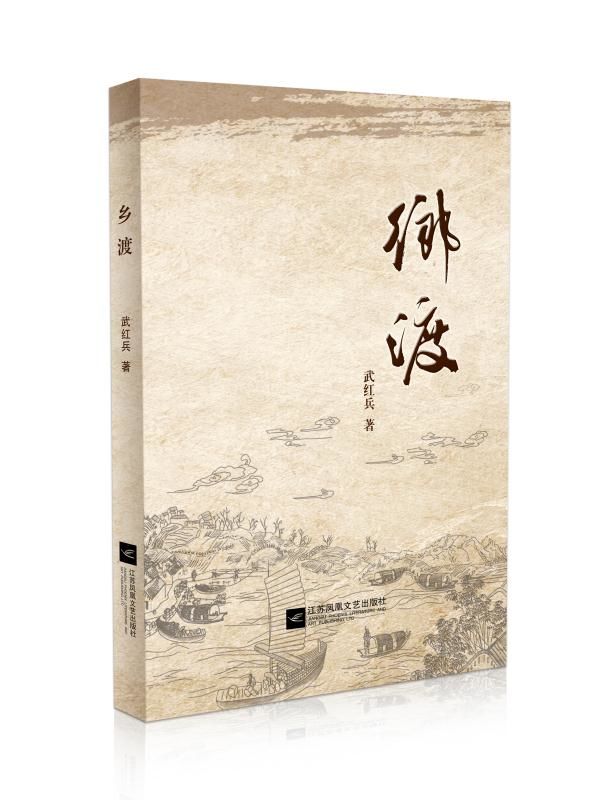
红兵老家门前有个“武障古渡”,他在这里从少年渡到成年,从乡村渡向都市,从当下渡向亘古,从俚语渡向诗境。
我的老家在古莞渎河畔的“陈何刘庄”,也有古渡,大致位于莞渎这个古海州东南第一镇旧址。记得上中学时,一次在陈老庄的同学家遇见杨圩的“孙大奶奶”,老人家听完我自我介绍后,说:“哦,你是河口刘家的啊?你爸小时候比你漂亮!”我这才知道我们庄还叫“河口”。既叫河口,且清末民初时那里设立过“莞南乡”,那想必当年该有个“莞南古渡”吧?那时,从武障古渡上船沿潮河向西里把路,拐进盐河再向南十来里,过新安镇再拐进莞渎河向东十来里,便是“莞南古渡”了。或从武障古渡沿潮河顺流东下,在三岔口拐进莞渎河逆流西上,也是可达“莞南古渡”的,里程差不多。水路这么便利,两渡的古远乡亲该是常走动的。遗憾的是因黄河夺淮入海,莞渎河自明清以来逐渐淤塞,到我童年时只剩些许断续河滩了。如今“莞南古渡”之于我早入梦境,虽梦她千回也未必能解我之忧;武障古渡之于红兵却成灯塔般的《乡渡》,引领他倾情海西故地,极目吴楚八方。羡煞。
文学总是深植于一定的文化土壤,表征该文化的经验与价值指涉,并反作用于该文化。作家所建构的文学文本是他所扎根的文化土壤的意义载体,意在再现这种文化想要信仰的那些符号与意义及其所蕴含的价值追求。它会潜心触摸这种文化建构价值秩序的每一次脉动,甚至艺术化地给出这种文化的基因图谱。这是文化认同的过程,审美的过程,也是特定文化共同体实践意识形态的过程。
文化认同向来发端于地域化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有赖于作家关于故乡文本的孜孜建构。童年的捞鱼摸虾和邻家饭香,勾勒了红兵的“舌尖上的故乡”,尤其是那独一无二的“虾籽”,仿佛记忆之“核”,瞬间就让我感受到了认同的巨大能量。“大于营”的徘徊、惆怅与不舍,也一下击中了我的情感深处,那儿也是我的“舅奶家”啊,我们童年最深切的血亲记忆,竟然如此高度吻合。社场点滴、对某个沟塘无来由的敬畏、对田园原生态瓜菜的无比惦念,则直指我们童年的隐秘之场。高考复读白描,一如我曾经写过的高考时《住旅馆》所感受到的城市“气味”,演绎的岂止是代代复写的寒窗之苦与“跳龙门”欲望,恐怕还有一种成长之痛隐隐可窥吧?割麦、戏水、打嘞嘞、叔嫂嬉等型构的麦收图,唱的是“田园牧歌”,怀念的却是我们曾经共享的、一去不返的农耕生态文明。这些文本似在告诉我们,童年与青春早已远去,童真与纯真却可以长久伴身,有了她们,故园的记忆俯拾皆是,故乡的云彩会常飘心头。
文学的价值追求是多元的,但古今中外作家在“民本”这一价值取向上,多能形成认同。民贵君轻也好,为民服务也罢,传承的都是千百年来人文知识分子念兹在兹的底层记忆。在这一点上,红兵用“小说化的散文”文本建构,带给我们异彩纷呈的“小城脸谱”。“吆喝汉”的洒脱笑脸,稀释了多少深巷艰辛。“油条摊守夜夫妻”的劳动者自信,诠释了平民幸福是怎样干出来的。“肉摊女当家”小眼睛里闪出的不光是生意上的精明周到,还有那为子女就业嫁娶而不辞辛劳的如意盘算。母亲出走、奶奶病亡、父亲车祸重伤的“护士站小男孩”,越是伶俐乖巧、聪慧好学和心怀理想,越折射出一个孤苦困厄的多难童年,好在还有萍水相逢的“王护士”、“武老师”们的点滴关爱在照亮他的前程。半个门脸水果店的“文艺范店主”,老夫妻俩收过粮食贩过猪,倒腾过蔬菜卖过鱼,说起一双儿女被培养成大学生是满脸骄傲,如今琴棋书画广场舞样样来,水果摊不过是他们玩文艺的小舞台而已,用他们的特立独行日日宣告:美满生活玩着过。小区空地“种闲花老太”很在意花开得热闹,更在意在她的花坛边向邻居传布她儿孙满堂的晚年幸福。“卖藕人”的每次悄悄“抹零”,不光是对老主顾的情感笼络,更有几分乡下人“胎里带”的憨直诚挚。小城古镇如此这般的烟火气,不光会勾起人们“清明上河图”情结,更型构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语境下故乡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千姿百态,指涉的是底层的生存法则和越来越近的幸福愿景。
建构身份自信的集体认同需要来自历史深处的可考记忆,而无论是大众的口口相传,还是高耸的广场纪念碑,能清晰告诉我们的不过是故乡区区百年的记忆纵深,更古远或更确凿的历史尚需我们穿过遗忘的帷幕,在大地河流、残砖断瓦、方志典籍中去追踪觅迹。红兵用“知识考古”来建构故乡的生命路线图,问来路,辨旅痕,理文脉,说兴亡。“故国寻踪”中城头村虽再难觅二千多年前汉城的县置轮廓,却也凭借城仓遗址、尹湾汉简确证了这片土地一度作为西汉侯邑的荣光。“硕项湖怀古”再现数百年前硕项湖这个百里大湖的潋滟,长吁的却是黄河夺淮入海后黄淮汇流所制造的大湖湮灭、洪涝蹂躏海西七百余年的无奈。远去的莞渎盐场因海而生,因盐而名,同样因为黄河的入侵而至大地年年生长、海岸岁岁东迁,失去了煮海之利,与莞渎镇、莞渎河相继消失在沧海桑田的巨变之中,也逼得因洪武赶散从苏州迁徙而来的灶民,不得不再次迁徙他乡。背靠大河千年的“大庙”,香火散尽,与附近新安镇上的
“九庵十八庙”一道消失,只留下些许村民视为生财珍宝的片瓦残础、“九里十八墩”传说和作家眺望对河古渡而生的禅思。共和国老兵的军功章与英烈的五封家书,则揭开了尘封已久的成千上万海西汉子慷慨悲歌、呼啸疆场、精忠报国革命史的一页。《乡渡》中此类清晰的寻古路线图,执着的典故文献考,以及虔诚的文脉忧思录,重构了对当下海西故地极具尊严与励志意义的证据,艺术而不失严谨地演绎了自己的来历和身份认同逻辑,间接回答了“我是谁”这个哲学之问——我们的故园海西,来自创世神话的冥想,来自沧海桑田的变迁,来自绝世苦难的洗礼,来自乱世迁徙的繁衍。我们是拓荒者,盐灶民,血性汉,治水人。
地域化的记忆离不开地域内外文本的互文。文本具有开放性和互涉性,不独文学文本,历史文本、哲学文本、政治文本等都是如此,任何文本都不是前所未有的史源性存在。文学文本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文本中某些东西先前已经被其他文本涉及,新的文本是已经写成的文本的回声与呼应,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止于此,互文性还凸显了一部作品在一种文化话语中的参与行迹,它与任何赋予该文本意义的语言、知识代码和文化表意实践之间相互指涉。这意味着,文本与前文本之间超越了单向度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成为全方位的多元互动的存在。在《乡渡》之前,或者说在《乡渡》创作过程中,红兵辑注了一部《海西诗境》,潜心注疏了古海西二百余首诗词歌赋。注疏的过程,是对经史子集、方志典故、碑文谱牒的广泛涉猎与研读,是神游古今、对话先贤、创构新话语的过程。经《海西诗境》的文脉梳理,才会有《乡渡》的怀古文游,诗赋唱和。《海西诗境》中的《酸枣令刘熊碑诗》之于《乡渡》中的《一块残碑千古事》、《盐河风帆》之于《盐河的帆影》等皆是表征。这样的互文性不单在作家古海西境内的踏破铁鞋中得到彰显,还在作家武汉访乡贤、闲凭西津渡、巢湖看清波、东林书院说冷清中瞥见苦心孤诣——戎马一生的武汉乡贤,祝福故乡的是永不忘却的粗粝土语;身在西津渡,遥忆的是武障渡;巢湖吃鳜鱼,念叨的是诗颂过古硕项湖的徽商方承训;漫游东林书院,寄情的却是古新安镇的卫公书院。即使是那些看似漫不经心的与妻游、与子游、与友游的小品闲章,不也是广涉海西内外千百年来绵延不绝的古风良俗么?
中学毕业三十余年来,因在异地工作生活,我和红兵相聚不过三五次、闲聊不过七八言,却因这《乡渡》而隔空作了一次穿越故乡古今的长谈。我这区区几千言和他的皇皇二十万言虽不相称,却也可算是互文性的一次彰显吧。
也是巧,近日听说红兵的孩子家也在南京河西南部、秦淮新河与长江相拥的鱼嘴地区,我们又不期相邻了。这鱼嘴是大胜关故地,也是古渡啊,莫非我们注定和古渡有缘?记得在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藏有一艘“渡江第一船”“京电号”,是从我们老家灌南寻得的。哪天打听一下它是怎么从盐河航到长江的?弄清航线,也许哪天我和红兵可以相约,弄条船,自大胜关古渡起航,历长江——大运河——盐河,或历长江——黄海——灌河,直抵武障古渡呢。
《乡渡》,渡乡。
作者简介:
武红兵,男,作家,连云港市散文协会理事,灌南县灯谜协会主席,出版散文集《乡渡》、辑注《海西诗境》(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等。
刘方冰,男,副研究员,吉林大学法律硕士、南京大学作家班毕业。作家、文化学者。创作领域与研究方向为:小说、文学批评、文化研究、法学、民国史等。发表、出版长篇小说《寇风烈》、文化研究专着《文化治理与监禁生态》等百余万字。参着部级课题理论专着6部,主编上海政法学院教材1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