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逝矣,雅韵长存。当代文章圣手汪曾祺笔下,呈给我们没有修饰过的一切,或曰经了修饰而不着痕迹的一切。汪曾祺脱俗又随俗。凡世间天然的情感种种,喜怒哀乐,食色男女,花鸟虫鱼,清风朗月,均在他那里获得新的生机。放在整个中国文学的大环境中考察,这也是不易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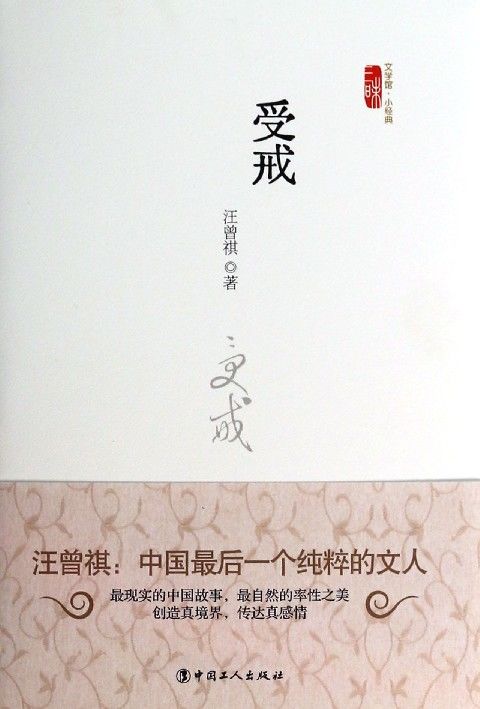

汪曾祺崇尚返朴归真。小说《受戒》里的荸荠庵,虽属佛门胜地,写来却是没有清规戒律的自由所在,遂成了一种象征,成了汪曾祺本人的桃花源、乌托邦。究其实它是作家本人的心灵幻象。汪曾祺无疑地有一颗仁爱之心,他的小说处处布满朋友情、夫妻情、父子情、乡邻情,人们相濡以沫、同舟共济、古道热肠;从秋日的山花,白发的母亲,敲磬的和尚,到井边打水的少女,无不氤氲着特有的温馨静美。读汪曾祺,不由要想起冰心的话:“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赠葛洛》)无疑,汪曾祺的作品是荫荫夏木,也是冬日暖暖的红泥小火炉。
《受戒》《大淖记事》开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小说新格局。在这类作品里,汪曾祺不重人物性格,而重氛围渲染,以玄远清丽真淳飘逸之气,表现健全的人性和健康的美。温软的水,朦胧的月,摇曳的云影,迷人的沙洲,感应着明海小和尚、小英子、巧云、十一子们细微神秘的心灵震颤;那混沌的爱,迷离的情,则展示出生命的腾踊,美的精魂的跃动。汪曾祺纤笔一枝,将人的自然情欲写得如此美绝人寰,一尘不染。《受戒》中明海与小英子的轻舟,最终浪漫地驶入江南水乡的芦花荡──驶向了汪曾祺情感的理想国和灵魂的伊甸园。清醒的意识流与自然的生活流的遇合,使得汪曾祺小说如行云流水,不拘不纵,真气贯注,而斧凿之痕全无。创作主体清风白水般的文化人格昭然可见。
汪曾祺写尽了水的明媚,所以在敏感的汉学家眼里,他满纸都是水。毋庸讳言,出生成长于水乡泽国的汪曾祺,与故乡水文化是有着一种神秘的交感互应的。柔情似水,佳期如梦;美丽的故事,淡淡的哀愁。六十多岁的人还能将文字写到这份上,简直称得上奇迹!汪曾祺是怀旧的。他对那些已经逝去和正在逝去的东西充满眷眷之情不舍之意。他迷恋漠漠轻寒,淡烟流水,自在飞花,无边丝雨;迷恋一切美好却不会再来的东西。他的许多作品,皆可视为“追忆”主题的叠加强化。
“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故人往事》)“来了一船瓜、一船颜色和欲望。一船是石头,比赛着棱角。也许━━一船鸟,一船百合花。深巷卖杏花。骆驼。骆驼的铃声在柳烟中摇荡。鸭子叫,一只通红的蜻蜓。”(《复仇》)“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受戒》)这不是小说,这是诗,是韵文;是东方意识流支配下的行云流水。事实上,汪曾祺作品确然打破了诗、散文、小说的界限,去除了诸般文体间的话语禁忌,以其浓酽的意象化和诗化特征,体现出东方美学之风神雅韵。
汪曾祺的小说散文,常如简洁疏朗的水墨画,更如朦胧幻美的成人童话。从这意义上,他很像安徒生,以纯情的笔调,表现人性的伟丽。他作品之超拔处,在于提供了一种纯如水晶洁如孩童清如琥珀亮如琉璃的文化人格。作为艺术多面手的汪曾祺,工诗擅文,能书善画。这使他触类旁通,为文下笔,常计白当黑,无字处亦成妙境;是故汪曾祺行文纵无机括,却能透彻玲珑,妙到毫颠,深得羚羊挂角之美。汪曾祺描摹物象,三言两语,便可跃然纸上,声光色俱佳。如他写高邮咸鸭蛋如何蛋白柔嫩,如何质细油多,真让人垂涎三尺,恨不能胁生双翅,一飞至高邮大快朵颐。这份出神入化的白描功夫,岂不惊人!除此,他还写了故乡的炒米、焦屑、咸菜、茨菇汤、虎头鲨、螺蛳、蚬子、野鸭、鹌鹑、斑鸠、蒌蒿、枸杞、荠菜、马齿苋……汪曾祺一而再再而三情深款款地追忆着它们,娓娓道来,如数家珍。这些故乡的食物,已然成为他情感的寄托。汪曾祺身在京都而心存高邮,时不时要灵魂出窍,作精神还乡。多么真淳的性情!
汪曾祺一支笔写尽平头百姓的欢欣,写活了小户人家的乐趣。这欢欣和乐趣像自在的水墨,在宣纸上稍一点染,即洇开来,成为迷蒙淡远的一片。他使人感到在这平凡尘世上,还有着若多诗意。汪曾祺是童心未泯的老顽童,也是可爱的、文雅的老饕;他在语言文字的厨房里忘情操作,其味津津,其兴勃勃。
有论者称汪曾祺作品缺少人文关怀,只是躲在象牙塔里抒写一己情感,纵为名家,难称大家。这话不无道理。然而,一个对家乡的草木枝叶、山水丘壑都关情备至的人,一个如此钟情自然和生活的人,怎么可能不热爱生命热爱人类,怎么可能没有人文关怀呢?桃李无言,下自成蹊。读汪曾祺文字,你会真正感动于生命之可爱,生活之芬芳;你会嗅到阳光与月光的气息。作为饱经中国文化薰沐的作家,汪曾祺的语言,承继了唐宋散文流风,更多明清小品余韵,复汲取民间文学之清新,轻盈流丽,小巧精致,如生生燕语,呖呖莺歌,滑而不腻,令人一读之下即悠然神往,远非某些吓人累人又唬人的“大散文”所可比拟。汪曾祺那信马由缰干净利索的文字,淡而有味,飘而不散,有初发芙蓉之美,无错彩镂金之赘,可谓俗极雅极,炉火纯青。这决定了汪曾祺作品无可置疑的文体学意义。
“我事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弄笔半纪,今已华发。成就甚少,无可矜夸。有何思想?实近儒家。人道其里,抒情其华。有何风格?兼容并纳。不今不古,文俗则雅。与人无争,性情通达。如此而已,实在无啥。”(汪曾祺:《我为什么写作》)汪曾祺以其文本谈天论地,谈人说己,坦坦荡荡,了无心机,像一个自足的隐者。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他是一个大隐。他的身上,有陶渊明的影子,却无陶氏“刑天舞干戚”的郁懑之气;有周作人的味道,却没有周那种自命的清矜。他笔势直追乃师沈从文,偶尔也受废名影响;颇得沈从文之清新,而舍废名之清冷。他从不以老人自居,时时如稚子野童,意气少年。他无意于做大师,只愿欢欢喜喜地做他的平民,做平民世界一分子。凡大师,往往因了生活在烟薰火燎之中而无法获得太从容、太纯的心境。汪曾祺遂显示出大师不具的特色。他的文字充满康德式的无功利性,美得纯粹,纯得惊人。他以浪漫唯美的态度静观一切,而远离充斥杀伐的文场,远离中心话语、政治漩涡;一切的飞扬浮躁急功近利叱咤风云赤膊上阵总与他绝缘。这种自觉的疏离,诚为一种心灵意义上的理性的主体选择。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文化人的大智慧大彻悟于此可见。
汪曾祺主笔的《沙家浜》,虽为“八个样板戏”之一,却仍能于红红火火中透出一丝那个时代难得的诗情雅趣:“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在当代文人里,汪曾祺是有斤有两定力极强的人,他始终对自己拎得很清。他和他的文章难称江河湖海,却是小溪流水,是溪水中清凌凌的白石细沙,活泼泼的游鱼小虾。“泉眼无声惜细流”,汪曾祺是静美的,然而静美中仍有鸢飞鱼跃,仍有生命之流的腾踊;不论生前,还是死后,汪曾祺都难以被摹仿和复制。
汪曾祺生得坦然,去得无憾。他是真正的士大夫,真正的思想者,也是人生大书的权威诠释者──尽管他从不在文章里摆开龙门阵大侃人生。汪曾祺是儒,是道,亦是佛;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这样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汪曾祺之后,复能有汪曾祺乎?“知音绝、弦断有谁听”,但愿其人其文,不会成为时代的《广陵散》,成为一曲文化绝响。
每想到汪曾祺,眼前便出现这样的图景:一个平和的长者,半卧于竹榻或半躺于藤椅上,对夕阳而独酌,忽会心以微笑。我总感觉他是晚唐的小李杜,虽然气象嫌小,但精雕细刻幽远深微自在清丽独成一体;何况他没有小李杜的颓唐。汪先生以自己的方式,对生命进行了诗意盎然的审美把握。他的文字是黄昏里饱含情感的生命独语,有青春气,却无迟暮气。
“双黄鸭蛋味道其实无特别处,还不就是个鸭蛋!只是切开之后,里面圆圆的两个黄,使人惊奇不已。”(《端午的鸭蛋》)这可以视为汪曾祺的自况。汪曾祺,就是这样一只双黄鸭蛋,总能“使人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