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云英,女,1933年7月28日出生,2019年2月28日谢世,目不识丁,辛劳一生,儿孙满堂。在苏北的大地上,这样的女性遍地都是。相信我,在未来的任何一部被称作“历史”的作品中,我们都不可能看到龚云英的身影。龚云英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她就是“百姓”中的一姓,现在,她的姓名被刻在了石头上,供她的子孙凭吊。
现在的问题是,历史是什么?常识告诉我们,历史是大事件,历史是大人物。这没错。历史只能是概括的,它不可能面面俱到。历史的书写首先面对的是符号化,只有那些被符号化的事和人才有可能成为“历史”。
这就导致了历史的余数,那个比历史本身要庞大得多、复杂得多、丰富得多和幽深得多的余数。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必然是这个:历史的余数有没有意义?
有。当然有。必须有。如果我们不能确认历史余数的意义,这等于说,我们就此否认了我们自身的意义,我们就此否认了生命的意义,存在的意义,乃至于活着的意义。但是,我们不习惯书写历史,我们认准了历史的书写是他者的行为与使命,我们一代又一代,就这样放弃了面对历史的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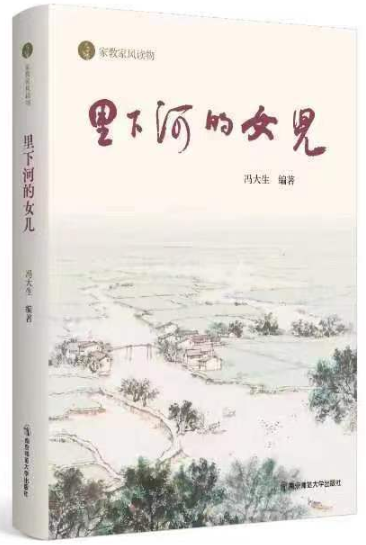
但是,有一个人,冯大生,我的本科师兄,他是一个异数。他另类。他不信邪。他坚持把历史书写的权利牢牢地把控在自己的手上——哪怕他书写的仅仅是余数。他的生母去世了,出于对母亲的爱,他写下了一篇又一篇感人至深的文章。这些文章称得上“文学作品”么?我不知道。这些文章够得上“历史书写”么?我也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冯大生不只是自己在书写,他还发动了整个家族,那些和“龚云英”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亲人们,他们一起来写。令人振奋的事情到底还是发生了,因为立体性和总揽性,那个普通的、目不识丁的、辛劳一生的、儿孙满堂的女性——龚云英——在我们的面前重新回到了三维,栩栩如生。她必将成为里下河大地上一段历史,一种生活,一种文化的生命范本。在长达86年的时间长河里,这里的大历史是如何转换的?这里的人们是如何婚丧嫁娶和生老病死的?这里的人们是如何劳作、如何持家、如何待客、如何助人、如何忍让、如何餐饮、如何教育、如何医疗、如何参与公共事业、如何“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历史”可以有断章,“历史”可以有跳跃,但是,生命,生活,没有一个24小时可以当作空白。回到先前的问题上来,冯大生这样做有意义就在于,他做了!而那些没有看到意义的人,仅仅是没有这样做。
如果我们愿意把这样的书写再拓宽一些,我们将不可避免地从“龚云英”的身上看到一个放大物,那就是龚云英和她的家。我们看到了一个完整家庭的运行和完整家庭的文化,这将给我们以启示,一个好人放大了,势必会带来一个好的家庭。
每一个个人的存在都是一部历史,历史学家可以宣布我们是余数,但我们不是。我们完成了历史,承担了历史,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历史。
作者简介:毕飞宇,当代着名作家,南京大学教授。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