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电子传媒的浮泛滥殇于科技搭建的互联网平台,而同质化的城市题材与科幻文学的复调介入,使文学生态的演进更加摇曳多姿。然则传统的地缘叙事作为曾经的文学范式之一,存与废,兴与衰,在时空交错中呈现出峰谷并峙的别样态势,作家李洁冰日前依托微信公众号“星月寮”写作坊,邀请中国计量大学人文与外语学院教授李惊涛(南宫宇),就地缘叙事文本在当代文学语境中的囿限与突围等进行了一次对话。由于两位作家是兄妹,对话饶有意趣,传递了人文知识分子的观照与思考。
一、文学创作呈现出更多的共时性状态
李洁冰:二十一世纪,全球化浪潮袭卷每个角落。文学作为一门叙事范式,在经历了十九世纪的经典叙事,二十世纪各种文学思潮及流派的演进,几乎穷尽了文学创作技法的探索。随着现代高科技、电子新媒体的泡沫式浮泛,晚近的文学写作又叠加了另一重挑战,即叙事场域已不再成为文本要素。经由城市题材、网络、科幻文学的复调辗压,更多衍生出类似“无根人”的文学多样生态。本次讨论的主题是,传统地缘叙事作为曾经的创作元素,是否已经日渐式微了,如何来看待它的囿限与突围?
李惊涛: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如果从历时性的角度着眼,是这样。但实际上,文学创作可能呈现出更多的共时性状态。新的写作形式、技巧或方法出现了,旧的范式并不一定会退场。它们会呈现出一种同时“在场”的现象。当下的文学写作场域,打个有缺陷的比方,就像一个大型火车站,好多火车开进来,都停在这里:货车有散货和集装箱,客车有绿皮车和动车……但写作是一种个体精神劳动,不容易也没必要达成共识,比如此刻,咱俩约定都不使用A而使用B方法,就很难做到。用什么方法,主要看具体作者的人生历程、情感遭遇、读书层次和偏好……就是说,他碰巧看到哪些作品,碰巧喜欢哪些作家,与个人趣好吻合,愿意受他影响,形成自己的写作观和方法,有很大的随机性。同属兄妹,但我们的写作题旨、语言路数和技巧方法,也不一样。即使是某个流派,比如法国的“新小说”派,貌似是一拨人,但细察后便知道,他们彼此间也有明显区别,像罗伯—格里耶和杜拉斯就很不一样 。因此我认为,文学写作场域更象是一种“纠缠”现象,即在同一个时空里,可能各种范式并存,比较符合实际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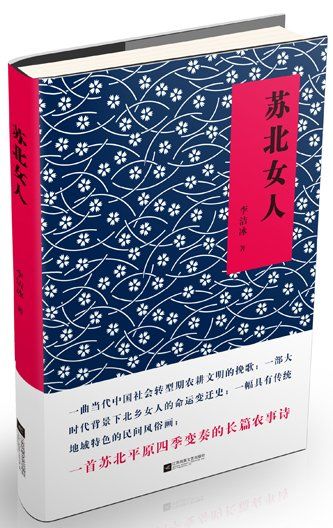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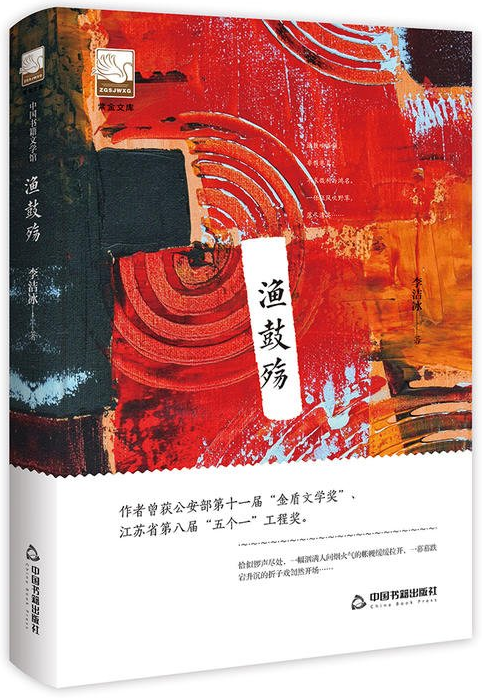
李洁冰:哦,这种解读是相对客观的。不过我更想追问的是,小说叙事场域的重要性问题,即传统的地缘叙事作为曾经的创作元素,就读者视野所见的当下文本中,似乎越来越难觅其踪,这是否意味着,由于上述原因的冲击,已不再构成写作的文本要素了?
李惊涛:是这样,写作的叙事场域固然重要。但要做个区分:第一,你指的是对作家创作心理构成深度影响的故乡,还是被他虚构在作品里那个被叙述的场域?第二,你所说的地缘叙事与叙事场域,似乎也不完全是同质概念。地缘叙事,更多指的是作家受故乡的地理影响,进而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更大的区域性特征吧。在我的认知心理中,叙事场域,是界定在作家于作品虚构的富有特征性的时空上,而地缘叙事则界定在作家受故乡的影响方面。
李洁冰:呵呵,我还真没想那么深远。作家的思维惯性,很多时候倾向于模糊表述。姑且以兄长界定的内涵和外延来讨论吧。比如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它对您的界定难道不是一种颠覆吗?
李惊涛:我是这么理解的:莫言在小说中出现的“高密东北乡”,与现实中的高密东北乡也不是同一概念,因为其中虚构的成分已经突破了现实囿限;而高密东北乡作为一种地缘叙事,对于莫言的叙事场域构成了显在和深入的影响。
李洁冰:有道理,在类似的维度上讨论,外延就宽泛多了,话题也可以打得更开。
李惊涛:我的基本认知是,叙事场域在小说写作中依然十分重要,依然是文本要素。我们所要讨论的,可能是地缘叙事的问题。就是有很多作家依靠地缘叙事取得了作品的经典性,而很多作家并不依靠地缘优势,同样也写出了很棒的作品。
李洁冰:这倒有点四两拨千斤呢。兄长不愧是搞理论研究的,话锋一转,就把问题切到您的思维频道上了,不过愿闻其详。
李惊涛:我注意到,你刚才提到“地缘叙事”时给了个前置定语,就是“传统的”;认为“传统的地缘叙事”在当下受到冲击,表现出所谓“式微”的征兆。这样理解对吗?如果是,我认为,地缘叙事,过去、现在、未来将会一直存在,因为它是以地域性特征获得表达优势的。它在当代文学语境中,是否隐含了自身生成过程中的某些囿限,呈现出需要突围的态势,这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与思考。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作为现象级别的问题,如果需要作家的个体去承载和消化,目前据我看,作家们还没有、也不太可能达成这种集体使命感或者共识。
李洁冰:是呀,这种概念辨析法挺有说服力的,但我仍未完全厘清楚。比如作家的辨识度,更多源自生命原发地的深层次浸洇:无论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镇,还是莫言的东北高密乡,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商州,阎连科的耙耧山脉,苏童的香椿树街,乃至江苏文坛新近崛起的“里下河”流派,作为承载理念的始发地,都镌刻着作家生命基因的内在肌理。这几乎成为文学生态的集体无意识。同时,我也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如京味,海派,津门等序列固然有分野,作家的创作也有“泛场域”的,比如余华,很难说他塑造的人物是海盐的,抑或浙江某地的。还有阿来,他笔下的人物与时空直接跟世界对接。也许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
二 地缘叙事与文学人物创造之间的辩证关系
李惊涛:余华的创作现象很有趣,我也注意到了,就是他写作使用的是标准普通话语汇,让你觉得他塑造的人物很难说是海盐或浙江某地的。《活着》被张艺谋改编为电影时,背景就直接平移到了秦晋一带,看上去也没有违和。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他接触和喜欢的文学作品,大多是翻译过来的,比如川端康成、卡夫卡、马尔克斯、福楼拜……译文使用的是现代标准汉语,也叫做普通话,是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作为语法规范的通用语;这样的表达范式,看得多了,会潜移默化,成为他创作时下意识使用的语言武库。二是他的家乡浙江海盐,有些方言语汇与普通话并不呈现完全匹配或隼接的现象。这就使得他在写作时,只好按下自己使用方言的冲动。他好像在创作谈中讲过这个现象。
李洁冰:这些桥段,还真得好好琢磨一下。它们几乎是歪打正着,让余华甩脱了方言这个窠臼,直接楔入了现代叙事语境。无论人物塑造还是语言,都形成了余氏特有的剥茧抽丝式写法。同时也成就了当代文学史上的余华。但某种程度上,这是否意味着许多作家对叙述中地缘优势的放弃,与其说是自主选择,毋宁说是出于某种机缘或无奈?

李惊涛: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有些无奈的因素。我的朋友,先锋作家张亦辉是浙江东阳人。他告诉我,在他的家乡切不可说某人“大眼睛”。在北方的普通话语汇里,这可是一种赞美啊!但在浙江东阳不是,据说“大眼睛”是骂人的。匪夷所思吧?你看,方言能否进入作家写作的语言武库,有时候真地受制于某些约定俗成的现象。我俩都是淮河以北生长的作家,普通话正是以北方官话为基础方言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受益了。即使如此,写到家乡一些谐趣的方言时,如果不加注,读者依然不能准确理解。比如“步撵”,说的是步行;由于“撵”的本意是“驱赶”,追加的释义是“追赶”,所以家兄认为,用“撵”并不准确,应该用“辇”,“步辇”就是“以步为辇”,即成语“安步当车”的意思,似乎也很贴切。
李洁冰:这就又回到我们前述所聊的话题,作家的气质,辩识度,语言风格由来有自,机缘巧合,与自然,人文其实都有着近乎神秘的关系。仅从这个角度,余华的创作给人们的感觉,即便抛弃了地缘特征的优势,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了。
李惊涛:依我的理解,余华使用规范的现代汉语语汇,是为自己增加了表达难度的。阿来的情况,或许也可以作如是观。他是藏族作家,使用藏语写作不是问题;但当他用汉语写作,便只能遵循现代汉语语法规范。可这个作家极为优秀,语言驾驭能力超强,以至于他用现代汉语写作,在我这个“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看来,不仅规范、流畅,而且美轮美奂,等于把“信达雅”给一勺烩了。
李洁冰:最后这个比喻很形象啊!我也特别喜欢阿来,他应该是当下国中为数不多融入世界语境的大作家。刚才,我们是从语言驾驭的角度讨论的。接下来,可以多聊一些人物塑造方面的话题。特别是对于作家这样的创作个体而言,地缘叙事与人物之间的辩证关系,您认为该如何定位呢?
李惊涛:你不是已经定位了?辩证关系啊(笑)。其实呢,地缘叙事对于人物塑造一定有深度影响的。比如你的长篇小说《苏北女人》塑造的柳采莲,就是个典型例子。她很像陈源斌《万家诉讼》里写的何碧秋;改成《秋菊打官司》的秋菊,也差不多,就是人物很“轴”。“轴”是苏北鲁南方言,大意是说人物性格特别执拗,一根筋,认死理。你看,无论是苏北作家笔下的柳采莲,还是安徽陈源斌的何碧秋,还是陕西张艺谋的秋菊,都一定是北方女子。所以我写的《“补天意识”的地域塑型》(见《扬子江评论》2019年第4期)一文中,特别讲到“地域塑型”,就是说的地缘叙事对于作家人物创造的影响,抑或反向表达似乎更确当,就是你致力于塑造出具有地缘特征的人物来。
李洁冰:是这样吗?对话似乎兜转到我的频道上了,这样聊起来相对轻松些。另外,您刚才所说的影响,既是线性的对应,也是块面的对应吧。
李惊涛:必须补充一点,线性的对应,指的是作家用自身的地缘理解对应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塑造;块面的对应则比较相对,在对人物性格的阶层和性别的表现上,会呈现出差异性。同样塑造农民形象,南方的鲁迅写的阿Q与北方的老舍写的祥子比,就狡黠多了。说到这里,我有些理解你为什么要说,传统的地缘叙事会呈现出“式微”的端倪,就是这样写来写去,终于有技穷的那一天:北方人憨直,南方人精明。所以酝酿突破,也就有合理性了。
李洁冰:但是这种现象,对于那些创造各种人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都能自如转换的伟大作家,也许并不构成问题。同样的鲁迅,不也写出过闰土这样木讷的农民吗?
李惊涛:所以,很可能问题的实质不在于作家塑造人物是不是受地缘叙事影响,而在于他想写出什么样的人物来。如果他要写的人物,是走南闯北、阅人无数的人;是游遍世界、见多识广的人,你又如何处理地缘在他身上打下的烙印?因此,关键可能是你如何有意识地利用地缘对于人物的影响,或者你笔下的人物性格的形成,如何受其所在的地缘和经历的影响;亦即你想要强调什么因素是重要的,你永远拥有自由,不必受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的干扰。鲁迅在《答〈北斗〉杂志社记者问》里说的“不相信‘小说作法’之类的东西”,大约也就是这个意思。
李洁冰:这样说,我好像又有信心了。十九世纪作为诸多大师的高光时代,将人类智慧绽放到了极致。后来者多因生存地缘的扁平化,鲜有大开大阖的生息背景,由此也失去了复制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无论是现代派,后现代派,碎片化,元叙述,零介入……这其间,叙事文本的自主探索与文学生态的被动演进互为杂糅。这种移步换景,背后的逻辑线是如何成立的;一个作家所面临的选择,究竟是遵从个人气质,还是顺应文学思潮的异变,在这方面,很想听听兄长的见解。
三、作家应遵从个人气质,谨防文学思潮的牵引与扰动
李惊涛:这个问题,从文学史中的现象与思潮的演绎中,可以理出一些头绪,虽然并不一定是逼近真相的。因为文学史都是后人修的。修史所依据的,既有作家作品,也有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艺术学、哲学、人文地理学和传播学等文献的交叉印证,还可以佐以相应的人物传记、创作谈、日记以及野史的综合支撑,再加上时间的筛汰、偶发性的触点和研究方法的更新,这些东西会让文学史视界里的很多观点和说法不断更新,次第影响着我们的理解与评价。因此,你才会得出前述的判断。但是在我看来,那个世纪里大师的高光,很多是我们人为赋予的。因为说到生存地缘的扁平化,十九世纪很多作家并不比我们强多少,比如法国作家福楼拜,其小说之光普照我们到现在,其实此人不过是一个偏居一隅的乡间地主而已,他甚至刻意要远离喧嚣的巴黎……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作家闭门就可以造车;塞林格把自己封闭起来以后,我们反而见不到比《麦田里的守望者》更好的作品了。我同意你所说的,“大开大阖的生息背景”有益于作家创作出波澜壮阔的叙事场域的观点,这从托尔斯泰、肖洛霍夫和罗曼·罗兰身上,都得到过有力印证。
李洁冰:兄长这番话,似乎透出哲学的辩证性来。但这种近乎浑圆的太极图一样的理念,稍不留神就会被“带节奏”,并不容易做直观的或直接的判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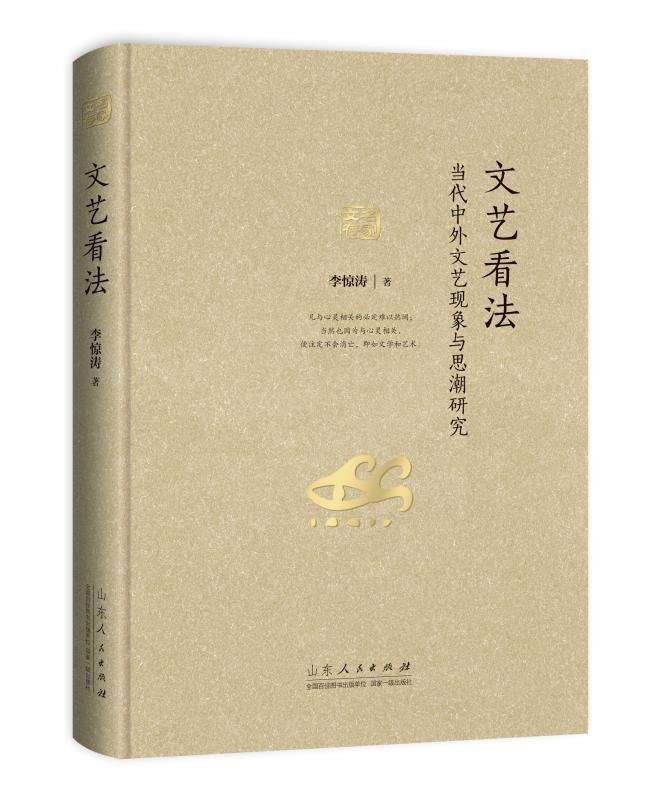
李惊涛:我是这样认为的,直观的或直接的判断,要舍弃很多例外、很多不利于形成判断的因素才可以做出来。我现在已经年届花甲,不愿意为了形成价值判断去割舍甚至无视一些不利于形成自己直观判断的重要事物了。当然文学史角度的文艺现象或思潮的粗线条,不是不可以画出来。比如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从浪漫主义到批判现实主义,再到自然主义,继而是现代派、后现代派……线索似乎也清楚。
李洁冰:聊到这里,我依然觉得,现实中除了极少数思辨性很强的作家,为数众多的写作者尤其是女性作家,其实是被直觉牵着走的。现代派或后现代派作品告别十九世纪的波澜壮阔后出现的那些碎片化、元叙述、零介入……等一系列方法、技巧和手段,究竟是叙事文本的自主探索,还是文学生态的被动演进;这些现象背后的逻辑线交错纷繁,除非你特别有定力,否则很难祛除影响的焦虑。在这方面,兄长不知作何解读?
李惊涛:逻辑线这个东西,一定是后人建立的。它是一个理性的产物,而文学史的现象更多是混沌的;其间可能隐含着更丰富多元、更偶然随机的因素。
李洁冰:所以,可否这样理解,文学生态的递进都是在各个时代峰高谷底,大浪叠起的时空背景下逶迤前行的,至于叙事文本的自主与收放,其信马游缰的程度何如,恐怕还是难以一言以蔽之。
李惊涛:是的。实际情况一定是复杂的,有触点和诱因。具体来说,古典主义之后的浪漫主义,便和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有关;浪漫主义之后的批判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便和英国乃至整个欧州的工业革命有关;批判现实主义之后的现代派,便和上个世纪的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现象与思潮的次第出现,又何尝不是这样。你可能注意到,我只排列了文学思潮和现象、流派出现的先后顺序,而没有像有些文学史家那样,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用“发展为”“进化为”“跃升为”之类的词汇。也就是说,我并不认为浪漫主义是古典主义的发展;同理,我也不认为“批判现实主义”比“浪漫主义”是个“进步”。这些价值判断的词汇,如果能够更多地从文学史描述中剔除一些,则可能会更接近真相。
从这个角度,现代派和后现代派所出现的碎片化、元叙述、零介入……也没有必要急于对它们做价值判断,认为是负面的东西。它们只是在文学现象或思潮中出现了,并且是新东西;它们与以前的东西之间,可能是“因果”的关系,也可能是“并列”的关系,当然,也不能排除某种程度的“递进”关系,比如说是为了“出新”才生成的现象。弗吉妮亚·沃尔芙就不喜欢巴尔扎克或司斯汤达那套现实主义手法,她奚落他们,刻意要颠覆他们,唱唱对台戏;而同为批判现实主义大师的福楼拜,是如假包换的现代小说鼻祖,他甚至认为巴尔扎克“不会叙述”,看不起他或为他惋惜;但浪漫主义大师雨果,就对现实主义小伙子巴尔扎克评价不低……
李洁冰:好啊,这种剥洋葱式的探讨,对于触及问题的深层蛮适用的。记得当年我在鲁院进修的时候,也曾接触过大量关于文学思潮方面的信息。饶有兴味的是,班上的学员当时按年龄、代际分出了好多风格派系。有的作家对新思潮天然承接,不存在任何障碍。也有人因为认知差异,已经产生了抗体。所以,即便是作家之间的对话也是困难的。这个话题见仁见智,确实有着无尽的探索空间。
李惊涛:是的,这种现象很值得思考。另外,你刚才说到“文本的自主探索”,我觉得更符合实情的说法,应该是“作家的自主探索”才是,文本只是呈现而已。而“文学生态的被动演进”的说法,我不太好评价。因为“文学生态”一词,在你那里很可能是个深思熟虑的概念,作为对文学存在现象综合因素的相互制衡、相互勾连、相互牵制、相互补给的一种认知,我也是能够接受的。而“演进”与“演化”比,词义更积极,带有更多的主动意味;你用“被动演进”来组合描述是很有趣的,一定有你的特殊想法。如果是我来界定,我会谨慎地使用“文学生态的自然呈现”这样的说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更倾向于作家要遵从个人气质,并谨防文学思潮对于自身创作的无谓牵引与扰动。因为思潮往往会“带节奏”,被“带”得多了,八面来风,反而晕头转向。如果你富有定力地观察、思考与表达,自身反而会成为现象,甚至引领思潮。

李惊涛:笔名南宫宇。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计量大学人文与外语学院中文系教授,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长篇小说《兄弟故事》、中短篇小说集《城市的背影》《三个深夜喝酒的人》、文艺论着《文艺看法》《作为文学表象的爱与生》、散文集《西窗》《赤塔之光》等着作行世。

李洁冰:作家,江苏连云港人。毕业于江苏师范大学外语专业。着有长篇小说《苏北女人》《青花灿烂》、《刑警马车》;中短篇小说集《魑魅之舞》《乡村戏子》《渔鼓殇》;人物传记《逐梦者》三部曲等。曾获公安部第11届“金盾文学奖”、江苏省第8、11届“五个一”工程奖;第5届“紫金山文学奖”、首届“朔方文学奖”等。中国作协会员,曾进修于鲁迅文学院第十三届作家高研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