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 者:您的《批评的返场》一书,整体分为“思潮”“作家”和“现场”三个部分。在今天这样媒介发达、信息爆炸的时代,每一天都有无数作家、作品涌入眼前,文学的“现场”也显得越来越杂芜。您是怎样挑选自己的研究对象的?
何 平:确实如你所说,文学的“现场”越来越杂芜。这是20世纪90年代文学市场化和世纪之交新传媒革命助推的——“人人都是写作者”,同时“人人也都是发布和传播者”的结果。网络新媒体赋予的审美平权,并没有带来预想的不同文学圈层的对话和交流,反而是不同文学圈层或多或少的“圈地自治”。这种“圈地自治”也可能发展为圈地自萌和圈地自嗨。每个文学圈层都受不同的力量左右,形成内在的运行机制和评价体系。举个最明显的例子,“网文圈”和“纸媒文学圈”,其平台、写作者、读者,甚至批评家几乎都没有交集。文学的分层和分众,导致的结果是没有一个批评家敢说自己充分了解今天文学的“现场”。怎样挑选自己的研究对象?取决于你究竟想做什么,在怎样的平台做,和什么人一起做,等等。比如这六年我做“花城关注”,《花城》的先锋文学传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指标。这样,“花城关注”的设定目标就是不断移动文学边界,拓殖文学疆域,尽可能地打开当下中国文学的写作现场,尽可能看到单数的独立的写作者在做什么,尽可能接纳更多新兴的作者及其文本,让不同的可能性、多样性和差异性一起浮出地表。我觉得“花城关注”最后让大家看到的文学“现场”,是我在不同文学圈层越境旅行中自然而然生成的,而不是预先挑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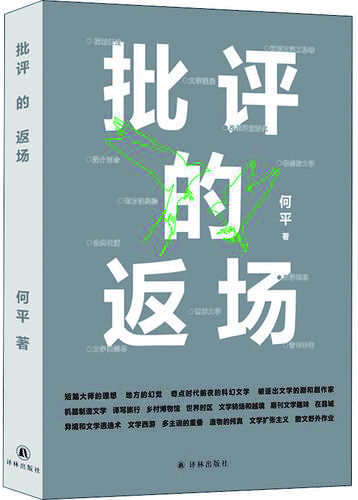
记 者:在该书的自序《返场:重建对话和行动的文学批评》中,您特别强调“重建文学批评的对话性”,并且重提90年代文学批评的对话传统。2017年起,您与金理教授共同主持的“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应该说就是这种对话性批评的一种实践。您认为在当下,还有哪些途径增强文学批评的对话性?
何 平:文学批评的对话性需要前提条件。我觉得有两点比较重要:其一,不能把文学简单地理解成文本为中心的写作、发表和阅读,而是应该扩张到更大的国民日常的文学生活,唤起文学激活日常生活和介入公共生活的力量;其二,对话性需要不断创造可资对话的公共空间。发表和发布的平台和媒介固然是公共空间,这个空间因为媒介革命已经释放出无限能量。但是,还可以转场到更大的公共生活。至于哪些途径能增强文学批评的对话性,就我自己而言,我现在做的“花城关注”的文学策展,“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寻找文学议题和公共议题的交集,召集不同身份和背景的青年人参与讨论,基本还是圈子里的事情。对话不能只是圈子里的人自说自话,而是要溢出和拓殖。更有效的和更广阔的途径是文学批评参与到国民文学教育、审美启蒙以及母语经典的普及。如果有所谓的文学出圈和破圈,这是应该努力的方向。
记 者:您强调“做写作者同时代的批评家”,书中关于阿来、新生代等的多篇作家作品论,尤其体现了这一特点。批评家与作家应该保持怎样的关系,其实一直是存在争议的话题。有人认为,要进一步增强彼此的良性互动,也有人认为,批评家与作家应该保持距离,这样才有可能保证批评的客观性。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何 平:现在说到“同时代人”都要提阿甘本。我对不熟悉的域外理论一直很谨慎。从阿甘本意义上的“同时代人”去理解中国当代文学并不容易,但至少阿甘本的这句话,“同时代性也就是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异联系,同时代性既附着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对我是有启发的。我谈过的作家远远不止阿来、迟子建、李洱、艾伟、邱华栋这五个,选择这五个与我相似的年龄所包含的相似的成长经验、文学教育、情感结构和思维方式等的作家做观察样本,也许更能提醒自己作为批评家的“保持距离”,他们和我的同与不同,他们之间各自的同与不同。
批评家在日常生活中是社会之一员。而一旦做文学批评,面对作家,当然应该有批评家的自觉、自律以及独立判断。不然,文学批评就等于是文学交际了。我相信读者和同行自有心中的尺度,是不是好的批评家,不只是自己说了算,也不是看你拿了什么奖。
记 者:2017年开始,您在《花城》杂志主持“花城关注”栏目,致力于寻找和发掘那些纯文学视野之外的作者,以及具有异质性的写作。几年以来,探讨了许多有意思的话题,比如导演和小说的可能性、科幻和现实、文学边境和多民族写作、海外新华语文学、摇滚和民谣,等等。您认为这样“小众”甚至“边缘”的写作具有怎样的价值?
何 平:“小众”和“边缘”对应的是“大众”和“中心”吗?如果是,“大众”和“中心”可能等于最大公约数、合并同类项,可能等于流俗、“躺平”和平庸,也可能等于因循守旧和创造力丧失。我曾经说过,现在的青年作家一出手就是“老年”态的文学,指的就是青年作家过于聪明和审时度势,他们的写作不是最大可能的审美冒犯,而是研究同时代文学“大众”和“中心”的位置。文学创造的心力用到了文学投机。而“小众”和“边缘”则可能保有个人性、异质性和可能性。你说的这些话题,有的是旧话重提,对当下重新检讨和赋予新义;有的则是时易世变,滋生的新方向和新疆域。我并不认为“小众”和“边缘”即正义。我唯一的标准是激活文学可能,释放审美能量,发明新兴文学。
记 者:您曾提出“文学策展”的概念,号召批评家借鉴艺术策展人的经验,主动介入文学现场,在文学写作中承担“联络、促成和分享者”的责任。这一观点对文学批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批评家对文学的现状和未来有一种整体性的认识和判断。可否请您展开谈谈?
何 平:你说的更高要求,算高吗?文学批评属于文学研究,自然离不开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支援,甚至也并排斥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研究范式,但问题是,如果文学批评等于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研究的书斋里学问,它的存在价值在哪儿?文学批评天生需要在场和在地。你能想象人类学和社会学不做田野?所以,我在讨论文学批评在大学学科建制的位置,建议文学批评向社会科学学习。现在做文学批评的,很少一部分参与到文学生产的第一现场,他们主持栏目,参与排榜和评奖,编辑文学选本等等,而另外很大的一部分的“现场”则是由这很少一部分人的“转述”,更有甚者是知网等电子资源提供的——对这很大一部分人而言,并不需要在第一现场,他们的文学批评是以论文写作为中心来组织和制造“文学现场”。“批评家对文学的现状和未来有一种整体性的认识和判断”是一个长期的不间断的工作。首先,第一步就是“下场”,到正在发生的文学生产中去,到文学的各个圈层去。就像你刚才提问所说,文学现场确实杂芜,每个人的文学现场都是有限度、短板和盲区,这就需要每一个文学批评家有文学公益心,需要文学批评界有协调和对话机制,共同做文学现场的“拼图”。“上海—南京双城工作坊”本意就是为上海和南京两个城市青年批评家建立一个常态的对话平台。
记 者:作为一名大学教授,您的本职工作是文学教学与文学研究。同时,您多年来始终站在当代文学的第一线,坚持以文学批评的方式对当下文学发声。两种身份是否偶尔出现矛盾?就具体的写作而言,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的异同在哪里?
何 平:这个问题上面已经谈到,文学研究有它的学术传统和研究范式,文学批评也一样有,但它们有共同的目标就是文学的经典化以及经典化的文学向国民文学生活的转场。对我个人而言,只是一个时间的分配而已。在一个大的学术制度下,你选择了大学教职,就意味着认同了它的游戏规则。我不太同意,将做项目写论文的文学研究和扎根现场的文学批评对立起来看。如果你想两者兼顾,就要考虑你做怎样的项目写怎样的论文,特别是年轻人,涉及到职业规划。而且,在现行的大学期刊等级制度下,发表文体相对自由的文学批评有很大的空间。所谓的顶刊、C刊和核心期刊并不排斥文学批评,甚至很多连摘要和关键词这些形式规范都不需要。事实上,很多时候不是刊物不包容不开放,而是文学批评从业者只能以一种论文腔的刻板论文,慢慢地改造了这些刊物的开放和包容。因此,基于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学术传统、研究范式、研究对象、表达的语体和修辞等等综合考量,大学的文学批评家是需要有多种研究生活和多副学术面孔的。我们看前辈学者们,几乎都是这样做,能做到的。
记 者:在今天这样去中心化的现实中,每个人所处的位置都决定了他所看到的、彼此不同的“文学场”,在您看来,今天的文学“场”由哪些要素构成?
何 平:说到“场”,其实是如何想象和建构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空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也自然有一时代之文学场。中国现代文学史,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文学“场”,是由作家、编辑、出版人、批评家和他们想象的有一定审美素养的读者构成的文学精英共同体。从1930年代编辑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就大致可以看出来。这些五四新文学的同路人,他们的文学圈有强烈的排他性,既排斥古典意义的旧文学,也排斥同时代仍然活着的旧文学趣味。这个文学场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中的边界移动和内部改造,熟悉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都很清楚。李陀说,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某些部分是小圈子文学,说的是这个文学精英共同体在新时期的修复和复活。今天讨论所谓文学的出圈和破圈,立足的也是这个文学共同体的精英和大众、雅和俗之分。有了这个背景,我们再看今天的文学场有哪些因素构成就很好回答了。大的文学场大致包括政治性的主题写作、面向大众读者市场的写作以及从精英共同体延长线上的所谓严肃文学写作,但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今天几乎没有一个严肃文学写作者不考虑大众读者市场,不然你就无法理解各家出版机构的竞价以及网红带货等等市场化行为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他们中的不少进入主题写作。而以“网文”为代表的面向大众读者市场的写作,慢慢发育出现实题材的“网文”类型的同时,一部分网络作家也在追求可以并轨到精英文学谱系的经典化。不同文学场既谨守各自文脉传统,同时也不断跨越边界,共同构成了今天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学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