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江苏作协“名师带徒”计划源于2018年10月省委、省政府《实施江苏文艺“名师带徒”计划工作方案》,共有20对文学名家与青年作家结为师徒。厚培沃土,春播秋收。在此,我们开设“‘名师带徒’计划成果展示”栏目,展现文学苏军薪火相传的良好态势。
一、葛芳简介

徒弟:葛芳
葛芳,1975年出生,毕业于苏州大学文学院,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协第五届、第六届签约作家。出版散文集《空庭》《隐约江南》《行走苏州 古镇乡村》《南极之南 远方之远》《文学创作方法谈》《漫游者的边境》,小说集《纸飞机》《六如偈》《白色之城》《给孤岛的羊毛裙》。曾获江苏省第四届紫金山文学奖。
二、葛芳创作成果展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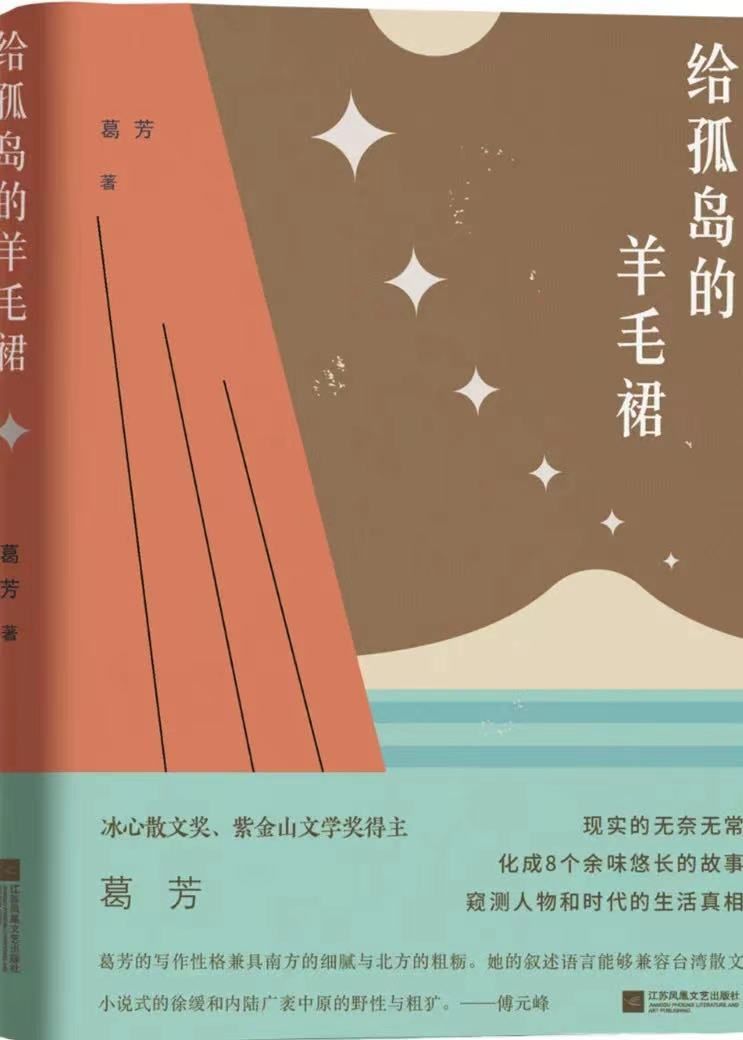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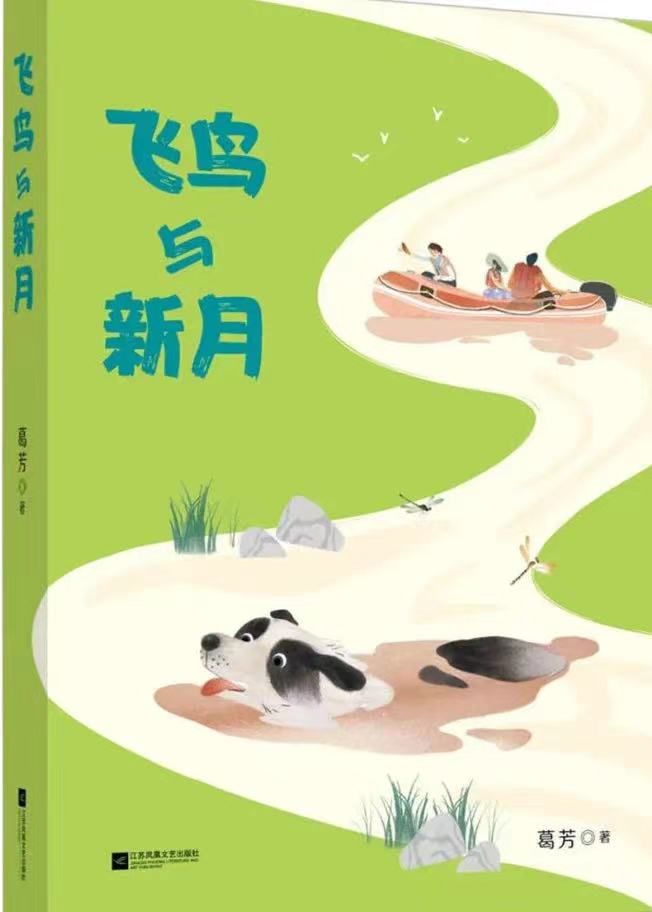
2019年
发表
短篇小说《要去莫斯塔尔吗》《白色之城》(《作品》2019年第1期)
短篇小说《安放》(《钟山》2019年第1期)
短篇小说《绣球花开》(《四川文学》2019年第4期)
短篇小说《幻影》(《长江文艺》2019年第7期)
短篇小说《空庭》(《雨花》2019年第7期)
短篇小说《消失于西班牙》(《上海文学》2019年第10期,《小说月报》2019年第12期转载)
中篇小说《铜雀关》(《星火》2019年第4期)
散文《巴黎墓园漫步》(《朔方》2019年第3期)
散文《巴尔干半岛笔记》(《黄河文学》2019年第3期)
出版
文学创作集《文学创作方法作家名师公开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6月
2020年
发表
短篇小说《长路山》(《雨花》2020年第2期,《小说选刊》2020年第4期转载)
短篇小说《飞翔的鱼》(《湖南文学》2020年第6期)
短篇小说《闯入者》(《作品》2020年第7期)
短篇小说《高棉的微笑》(《大家》2020年第5期,转载于《小说月报 大字版》)
中篇小说《我要从南走到北》(《飞天》2020年第4期)
出版
小说集《白色之城》,安徽文艺出版社,2020年9月
2021年
发表
短篇小说《只是朱颜改》(《作品》2021年第4期)
短篇小说《云步》(《上海文学》2021年第7期)
中篇小说《垂钓声音》(《芙蓉》2021年第3期)
出版
散文集《漫游者的边境》,中国言实出版社,2020年1月
长篇小说《飞鸟与新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4月
小说集《给孤岛的羊毛裙》,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7月
三、葛芳作品
云步(节选)
3
林平山的扮相实在是堪称惊艳。
长得俊,再加上化妆师笔墨点染,在舞台上,水袖一闪,别说女人心动,连男人看了也会爱煞。昆曲里的曲词又是雅极,光听那曲牌名,就让人浮想联翩,什么玉山颓、醉扶归、霜天晓角、桂花锁南枝,一个个场景让人恍若到了另一个世界。
《琴挑》那折戏,林平山面对小旦百转千回、满是妩媚的“啐”字,稳稳当当迎上去一个字“喏”,包容默契,且也是无限恩爱。男女水袖交织在一起,情思缠绕,台下无一人不说好。他才十八岁,把戏里男女感情拿捏得如此精准,连教他的老师也忍不住点头。
省城三年时光,为了演好戏,他吃了不少苦头。刚开学第一学期,他偷跑回家,抱怨说唱戏太苦了,寒冬腊月要压腿练台步,要吊嗓子,他不想再继续了。
母亲沉下脸,蹲在河埠头拉着老咸菜的菜帮子说:“哪一门不苦?去了就不好放弃!”
母亲的话不多,但含着人生的哲理,把平山逼回了戏曲学校,他想是啊,二叔是炮兵,他走在一人深的野草间毫无恐惧感,那里满地弹壳,水沟里到处飘溢着腥臭味,血水滴滴答答从罅隙里流出。敌机在轰鸣,越来越近,他的双脚却被杂草绊住了,根本不能向前跨出半步——炸弹落在他头顶上方,蘑菇一样开花,你看,二叔到死都没有放弃。
回到学校,他比以往更努力,很快被老师宠着,被女生围着追。程心佑是追他追得最厉害的女生,她爸爸在省政府大院里办公,可林平山的心思全在演戏上。
在舞台上他脚步轻轻移动,水袖翻飞时,他想另一个自己躺在几百里外的棺木中安静地睡觉。他的眉眼上抬,棺木里的自己也眉眼上抬,他的喉咙传出旖旎的称呼“啊,姐姐——”棺木里的他也在轻轻呼唤,呼唤当初的女朋友的名字,“啊,小菊——”
对。平山特意去见过大西宅的小脚老太小菊,她身材矮小,满脸皱褶,靠在墙角根看两只母鸡啄地上的米粒。他喊了她一声:“小菊婶婶!”她纹丝不动,没听见,耳背,一点也没反应。他怔怔地,心想,这是二叔曾经喜欢过的有藕节一样胳膊的小菊吗?
年轻时的小菊,一定鲜嫩得掐得出水。所有美的、青春的,都是这样惹人怜爱。
有一次,老师心血来潮让他扮演旦角。服装、头饰统统到位后,全场的人都敛声屏息,活脱脱一个妙龄女子,身材高挑,粉面桃花,云步,水袖绵延出万般思绪,水磨腔伴着笛声,竟是如此柔美!
“袅情丝吹来闲庭院——”光是一句就足够有味道了,是百无聊赖中的浑身酥软,是江南细雨中的气若游丝。
抬头望镜中的女子扮相,林平山也着实吓了一跳。这是自己吗?好像是,又是另一个自己?太阴柔美了,他不喜欢,他不喜欢自己太女人气,他需要自己刚性,再阳刚些,要气吞万里,要虎虎有神。
他扯下头饰,换掉服装,将搪瓷缸里一大壶绿茶喝掉。程心佑到化妆间,约他去爬明城墙。明城墙适合晚上去爬,一轮明月,一群男女唱着歌儿拾级而上。程心佑说她妈妈做了不少点心,蒸饺、烧卖、小米糕,带了一箩筐,拿到城墙上分着吃。
林平山惦记着同玄镇的点心,萝卜丝饼、粢饭糕、酱瓜、山药糕……他说:“我老家的点心才有味道,比你们省城的好吃得多。可远水解不了近渴,到时凑合着吃吧。”俩人兴冲冲去了,等了半天不见其他人来爬,程心佑才羞答答告知:“不用等了,他们不来,就我俩……一起看月亮。”
他俩背靠背坐在城墙上,那轮月亮不够丰盈,但迷蒙得很,林平山的脑海里又跳出二叔的话,“那年年初,媒婆把她的照片送到我家里时,我心里是一百个喜欢。都讲好了,等明年年末,等我部队回来,就完婚。”
林平山的心一紧,二叔如果没有阵亡,娶了喜欢的女孩该多好。
程心佑拽着城墙砖缝里的草,柔声说:“我喜欢你很久了……”女追男,隔层纱,要这样实实在在吐露出来也不容易。林平山回过身体伸长胳膊,将程心佑搂在怀里,他想着,二叔把小菊姑娘终于搂住了。
一半虚幻,一半真实,他们在月光下开始缱绻,仿佛戏里的一对,白素贞与许仙,杜丽娘与柳梦梅,杨玉环与唐明皇,反正,愿意是哪一对,就哪一对好了。
4
林平山慢悠悠踱方步回到同玄镇平山工作室。
另一屋子里有七八个孩子在咿呀练唱,童声娇柔中含着脆生生,像霜冻以后的萝卜,滋味特别好。这些孩子跟了他两年,进步不小。
平山每两周回同玄镇一次,主要是惦念着古镇上的气息,苋菜馅儿的烧饼刚从炉子里取出,飘得整条胭脂街都是;河水哗哗地流,鱼儿跃出水面“啪嗒”的声响;他闭着眼也能从街东走到街西,不会掉进河里,不会撞到哪块青石台阶。
教孩子唱昆曲,是政府资助工作室成立后的事,他也欢喜,言传身教,看孩子们晶亮亮的眼睛,看一双双肉嘟嘟的小手跷起兰花指,真有天生的喜感,倒是让他忘记了很多烦人的俗事。
昆曲这艺术,说白了,要传承,不传承就会断了根,就会像浮萍,漂着漂着没了影踪。
程心佑多年前就改行了,她开服装公司,开化妆品店,她的观点是要赚就要赚女人和孩子的钱,赚得合情合理。程心佑自己就是衣架子,标准身材加标致面孔,公司形象大使,没得说。
程心佑枕边风吹过很多回:“别唱了,没前途的,有多少听众啊!成天面对老头老太皱巴巴的面孔,抖抖索索,哦呦,自己也变得酸腐气了。”
林平山不吱声。
他们家里一直都是程心佑在指手画脚,该买个大一点的房子啦!该买一些基金理财!该给女儿上最好的私立小学!林平山不说话,只做自己的主——下一场他要全力以赴演好唐明皇,去感受他在马嵬坡无奈惶恐到极致的心情。一招一式,一呼一吸,一字一顿,都是人生面临崩坍的迹象。
“真是三拳头打不出一个闷屁!”程心佑气鼓鼓说道。恼怒之余索性不跟他商量,再加上她小姐妹也多,没事就一起外头开心逍遥,经常玩到深夜回来,高跟鞋东一只西一只胡乱扔,倒头就睡。
林平山面对一面墙闭眼睡觉。他听见另外一个自己在棺木里说话:“透过阴宅的窗户,我能隐隐约约看见院子里的泡桐树,树上有鸽子在扑动翅膀,忽然间全都飞起来,在水渠上盘旋转圈。”
他从来没有和程心佑说起过二叔的事,她一定不感兴趣,而且会觉得他脑子出问题了。他也没有必要告诉她,这是他自己的事,是他和另一个自己的事,他不想让任何人介入。
“我舒舒服服将我的手脚伸展开来,我用战争残留给我的一只耳朵凝神听着,听窗外的风声、雨声、鸟啼声和村人耕作时的闲谈声……光线在变化、四季在交替,通过这比巴掌大一点的窗户我都能感知到。我并没有死去,我的肉体还在,这表明我还能思想,能感知我所热爱的这块土地上的一切生灵。”
二叔的棺木在平地之上,一米高的阴宅有窗没有门。
平山心想幸亏没有彻底埋在土下,否则哪有光线?他小时候就最怕黑,黑咕隆咚,伸手不见五指的黑会把他逼疯。
夫妻俩各自忙,一个忙生意,一个忙演出,孩子丢给外公外婆,一家人团聚的时间很少,好像夫妻情分、亲子关系也不是那么浓了。
反而是回到同玄镇工作室,一接触这些孩子们,林平山的心绪就安静得很,不想其他事情。
晚饭喝粥。林平山在工作室用文火慢慢熬,人站在旁边,用勺子慢慢调,看粥渐趋黏稠。手上还拿着本书画,读扬州八怪里一怪——高翔。
“匡床自在拥寒衾,卧听儿读妻织履”,林平山一字一字体会,多有市井生活气啊!浸润着丝丝凉意的清晨,妻子在窗下盈盈编鞋,勤学的儿子也借着晨光,在院子里稚声稚气地诵读着功课,作为丈夫的高翔拥裹着被子,还在床上闭目养神。
古人真是惬意慵懒。林平山伸了伸腿,生活上的情态他已经不做奢求。
如今他在乎一个人的时光,工作室临河,开窗就是古运河,水声欸乃,还有船只经过,他泡好一壶茶,萧萧瑟瑟地看河水涌动,一寸寸里亮着光泽。
他想起五年前在省城日日夜夜排练《牡丹亭》的情景。为了挽救昆曲,改变它不死不活的现状,让它焕发青春活力,让更多的青年观众接受,林平山也是下足了工夫,当领导让他饰演柳梦梅,而且下任务要演出全新的柳梦梅时,他也默然应允了。
于是开始在花花草草间腾挪,将那一声“我嫡嫡亲亲的姐姐啊!”不知呼唤过多少回。偶尔,他的念头会飞快地闪现过躺在棺木里的二叔,他也青春着,永远二十三岁,定格在那个时刻。
那么他林平山就是几个人的化身,他们都在喊“我嫡嫡亲亲的姐姐啊!”每每这时,林平山在舞台上的表现完全凭直觉,一举手一投足都好看极了。行云流水,洋洋洒洒,别有韵味,连唱腔也独有他的味道。青春忧愁的气息在升腾。他含情脉脉,两颊粉色,比杜丽娘还有柔情几倍,全场的观众像茶叶一样在水中舒展开来。
(原文全文刊登于《上海文学》2021年第7期)
四、名师点评

结对名师:杨守松
杨守松,报告文学作家、散文家,曾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
云和梦依然存在
因为我在昆曲里面浸淫多年,当然希望“徒弟”关注昆曲,最好也写昆曲,但是,内心委实有点嘀咕:千万千万,不能为了写昆曲而写昆曲!因为我真实的想法从来都是:不可能也没必要每个人都去喜欢或者关注昆曲,我说的仅仅是:你可以不喜欢,但你不可以不知道——一般而言,知道就好,知道了至少就不会无视甚至亵渎了中国文化一个图腾一个名片。可是,我没有这么说,因为我觉得对葛芳而言,根本不需要我说,或者,还有那么一点点小心思:看葛芳如何“写”昆曲吧。
几个月后,葛芳把小说《云步》发来了。十多年了,只看昆曲,没看过一篇小说。可是这回不一样。这是省作协布置的“任务”,是所有“名师”带徒必须要做的“功课”:师徒对话等等。还有,她写的是昆曲呢!于是就看了,漫不经心地看,谁知,看看就被吸引了,久违了的小说慢慢就把我带到一个“云”的世界了——不是云里雾里,而是云里梦里:汤翁四梦,小说其实也写了林平山的梦,一个坚守在舞台上的昆曲人的梦。
然而,“舞台上生生死死由人恋,可真实的婚姻竟如此不堪一击”。林平山唱戏唱“傻”了,妻子程心佑移情别恋,先是分居,而后分手。无论是分居还是分手,林平山都见得出奇的平静,平静得不近人情,木讷,还有点傻。
很欣赏“二叔”这个情节的设置,尤其是林平山与“二叔”的对话,为梦的题旨注入了厚度。这个“二叔”(后来葛芳说生活中的确有过)死在战场上,他的棺材一直留着,“阴宅”的存在给予小说无限的想象空间。林平山与二叔的对话贯穿小说始终。生与死、虚与实、现实与梦境的对话。小说的主题,正是在林的坚守和追求的“云”里面完成的,是在生与死的阴阳两界的灵魂交错甚至是交媾中完成的。
昆曲便是“云”,是云步,是水袖,是云里梦里的化境。
哪怕崇祯皇帝煤山陨灭(《铁冠图》),而柳梦梅的生死恋情依然鲜活,依然在大梅树下绽放(《牡丹亭》)……
小说的氛围充满了淡淡的忧愁,淡淡的哀伤与迷茫,即便坚持和坚守,也是淡淡的,波澜不惊,云淡风轻的感觉。不仅仅是妻子的离去,还有评弹艺术的衰颓,以及小菊对二叔的永生永世的痴情,最终,因为征地拆迁,二叔的“阴宅”(棺材)被焚烧,小说在看似沉重却又蕴含着波涛汹涌一往无前的“高潮”中戛然而止。
云和梦依然存在,就如《牡丹亭》,主人翁向死而生,林平山向死而生。
《云步》写得真好。
回到开头,作家带徒,某种意义上是个悖论。作家是不可能如表演艺术家那样,一对一带徒“传承”的,更何况,至少就小说而言,葛芳比我写得好,她是我“师傅”啊。如今这么颠倒过来,也只好勉为其难——我对葛芳说,有时间过来我这边坐坐,我们不谈小说,不谈文学,就聊天说昆曲吧!
因为《云步》写了昆曲,所以也就难分难解,就这么说了说,结果就有了这个“读后感”似的短文。
2021.3.23
五、师徒对谈
醐途楼漫谈文学与昆曲
前言
仲春时节,我们驱车来到昆曲古镇巴城。老街上行人不多,粉墙黛瓦上悬挂着的红灯笼显得格外醒目。桥那边油菜花开得正旺,隐约中能听见鸡叫,老街小巷尽头是一条运河,十几条机帆船连在一起蔚为壮观。青石板流淌着古意,一脚一脚踩下去能感受到岁月的印迹。酒楼的一副对联将活泼泼的民间气息显露“老街一夜雨,酒楼十里香”。我们有关文学和昆曲的谈话也在这惬意的氛围中展开了。(葛芳)
杨守松:我在文联十八年,建“糊涂楼”,留下三百首“糊涂诗”。退休后至巴城,曰“醐途楼",专门与昆曲人交往,“竹林”留下海内外近二百昆曲人签名。这十五年来都浸泡在昆曲世界里,和写作的人几乎不打交道。
这次省作协“名师带徒”让我和你成为师生,也是缘分。我主要写报告文学和散文,对小说研究不多。你最近创作的小说《云步》,以昆曲演员为主人公,我看了,小说写得不错,昆曲你是理解了,而且理解到点子上,不少人只懂一点昆曲皮毛,就耀武扬威很讨厌。昆曲并不是人人都知晓,但作为作家要知道,它是文化人玩出来,是真正文人雅士做的事。
600年前,元朝末年,儒商顾阿瑛建造了一座玉山佳处,邀请天下文人雅集前来,弦乐歌舞,诗酒唱和。庞大的园林,厉害的家班,全国80%的文人都来到此地,着名的玉山雅集前后收集了5000多首诗文,这都是最顶尖的文化人在一起玩,推动了昆曲的发展。
到了明朝,文化人基本都是昆曲迷。文徵明可以可以一个月不洗脚,但不能一天不听昆曲。唐伯虎专门画昆曲戏。
当然尤其是到了清朝,文化人专属的昆曲,慢慢成了皇帝的专属,在宫廷中昆曲得到了高度重视。《红楼梦》小说中就有几十个地方提到昆曲剧目,比如我们熟知的《豪宴》《乞巧》《仙缘》《离魂》四出暗伏着全书的大关键;《满床笏》和《南柯梦》隐藏着贾府的兴旺与落败。而黛玉深埋心底的惆怅将我们满满包围的那一刻,正是她听《牡丹亭》的那一刻——“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你在幽闺自怜”。可见,昆曲的业界地位相当之高。
葛芳:确实昆曲的词雅到了极致,要有一定文化水准才能创作出来。
葛芳:我最近创作的几篇小说都是以江南地域文化为背景,一个地域,就是一方文化。尤其咱们苏州,是风雅之城。我想把代表性的江南元素如昆曲、评弹、古琴都作为背景展开,形成若有似无的氛围,为此我也采访了一些相关演员、专家。就这个刚写好的《云步》,不知道昆曲元素在小说中是否拿捏到位?
杨守松:我觉得把握得挺好,这些昆曲素材你是巧妙化用进去了,不生硬,譬如《牡丹亭》《铁冠图》这些经典曲目,你都能很自然的放进故事中。汤翁临川四梦,写得也是人鬼灵魂之间的对话。你这个小说中昆曲演员林平山和二叔两个人的对话设计得特别巧妙。二叔是个烈士,已经死了,但遗体保存着躺在棺木中。两者之间的对话把人物关系一步步向前推,对人物形象塑造很有帮助。不仅想象奇特,而且把昆曲人对艺术的坚守、人生历练后的从容表现得很充分。譬如说这个主人公林平山对爱情的态度,因为入戏太深,在生活中处理婚姻问题也很特别。那么大的波折,却在他眼里似乎波澜不惊了,这样就很符合人物性格和身份。
小说的结尾也符合生活常理,再怎么纠结的事情再怎么宏大的背景,都抵挡不过时代的洪流。你小说中引用的几段昆曲唱词也能准确把人物的种种滋味表现出来。
葛芳:对,文化元素要化开来写,精准到位,譬如陆文夫的《美食家》。千万不能在小说中强插,卖弄学识一番去炫耀,那就会倒胃口,读者也不会喜欢读。
杨守松:你这小说还表现了青春与死亡的对抗。青春虽然是短暂的,但让人无限依恋,杜丽娘因为对青春的眷恋抑郁而疾,但也因为一往情深而由死复生。二叔在最青春的时候死去,却他永远活在林平山的心中,而且到达合二为一的地步。这种浪漫主义手法处理得很好,合情合理。
葛芳:杨老师您醐途楼上的对联倒是很准确地表述了人生和戏曲的关系:“人生如戏无非生旦净末丑,戏如人生最是酸甜苦辣咸。”
杨守松:是的,好的演员必须跟文人交朋友。光凭借漂亮面孔是深入不了的,演员只是一种职业,是一种生存方式,要成为好的演员,那必须在人品上有高的境界和修为。我刚研究昆曲的时候,原以为昆曲十分神圣,研究进去了以后,发现昆曲圈里什么人都有。写作圈也是。所以,好的人品至关重要。
葛芳:我过来的时候,经过一片清澈的湖,高德地图上显示是傀儡湖,您这儿墙上挂着一行名家写的字:“昆曲源头就是傀儡湖”,您能给我开讲一下吗?
杨守松:相传昆山腔起于唐玄宗时的乐师黄幡绰,他以善演诙谐滑稽的“参军戏”,与善歌的李龟年、善琵琶的贺怀智等人并立于宫廷。而后安史之乱爆发,大唐盛极而衰,黄幡绰随叛军去,回后被关押,唐玄宗向儿子(皇帝)求情放了他。他流落到江南…(白居易有诗言及此事,一说李龟年一说黄幡绰)饱经丧乱的黄幡绰流落至此,在湖边演唱傀儡戏(参军戏的一种表演形式),并且开馆传艺。黄幡绰死后葬于此地,湖成了“傀儡湖”,埋葬他的山就成了“绰墩山”。
葛芳:一个小镇,深藏着古老的文化,真是罕见啊!
杨守松:昆曲在小镇上真正懂它的人还不算多,属于小众,因为昆曲文化曾经断层过。只是靠民间堂名在婚丧红白喜庆时吹拉弹唱保留了一些,靠官方推动的很少。随着传统文化的兴起,政府扶持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多,巴城镇从很小规模的重阳曲会,一步步发展到今天远近闻名的“昆曲小镇”。一年四季都有海内外的曲友、演员来巴城以曲会友,周边大学的留学生甚至经常来学唱、“打卡”。
“吴越春秋写昆剧,时人尽道雪艳词。英雄美人两相惜,成就千古《浣纱记》。”我把梁辰鱼的《浣纱记》重新选编,去年十月份进行首演,接下去会进一步完善。
葛芳:我准备下一个小说创作以古琴等文化元素为背景,前两天刚刚采访了吴门琴派的裴金宝老师。
杨守松:古人琴棋书画都通,是真正的文化人。今人能这样的很少,虞山派传承人朱曦,有这种气质。裴金宝老师也相当不错,德艺双馨。作家一定不能被名和利束缚了自己。要坚持自己人格独立,写出有力量的文学作品。